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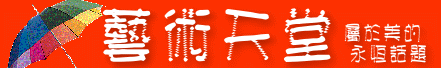 |
|
|
|
|
李錦繡的「空竹凳」 陳韻琳 |
|
前註:為了尊重創作版權,所有的圖片都僅用來作文字的說明,故意照的不清晰並且將朋友攝入畫面。  這次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的「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2005.09.03-11.27),我第一次進展覽會場時,便對展覽李錦繡藝術的整體空間的設計,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後,我從《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展覽專輯中發現,這次紀念展的策展人是當代藝術家王素峰女士,展場空間規畫有她細膩的設計意涵。我也非常感動於王素峰為了籌畫這次展覽,所做的種種預備,包括深入訪談跟李錦繡有關的親朋同學、整理李錦繡的手稿資料,以及最重要的,從藝術作品嘗試認識李錦繡這個人,其熟悉度從素昧平生到如同閨中密友,使我有很多的感觸。
這次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的「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2005.09.03-11.27),我第一次進展覽會場時,便對展覽李錦繡藝術的整體空間的設計,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後,我從《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展覽專輯中發現,這次紀念展的策展人是當代藝術家王素峰女士,展場空間規畫有她細膩的設計意涵。我也非常感動於王素峰為了籌畫這次展覽,所做的種種預備,包括深入訪談跟李錦繡有關的親朋同學、整理李錦繡的手稿資料,以及最重要的,從藝術作品嘗試認識李錦繡這個人,其熟悉度從素昧平生到如同閨中密友,使我有很多的感觸。 當然,我這麼積極主動的想介紹李錦繡,一樣是因為她的藝術作品深深感動了我,它們彷彿在跟我說話、呼喚我一般,使我無法自拔的被作品吸引,因而能稍稍進入她的心靈世界,彷彿已成為她的朋友。 因此,在談到李錦繡的藝術作品之前,我想先把王素峰這位藝術家透過展場裝置,意圖呈現出來的李錦繡的創作心靈,跟大家分享,這些現場裝置,在我看來,本身也是藝術,是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的對話與共鳴。 王素峰在展示李錦繡作品第一分期主題「虛幻的人生」時,讓展覽室直接看到第三分期「自覺的舞動」的代表作品「生命」。 王素峰對李錦繡作品的理解是:虛幻性、曖昧性、透明性、穿越性、移動性,因此她的裝置藝術,透過有透明玻璃、毛玻璃的小框框,讓我們可以從這頭,穿過框框的玻璃,看見那頭,因而產生出虛幻性、曖昧性、透明性、穿越性、移動性的感覺。這設計成為一種既有變化又統一的風格,在李錦繡不同藝術分期中都出現,以作為一種對李錦繡生命藝術的回應。 虛幻的人生  如果要我將李錦繡這一生的創作主題抓出主軸,我抓到的是探詢捕捉空間、與探詢表達自我的雙重奏。 李錦繡最早期1972-82的繪畫作品中,色彩表現分期裂斷成兩半。她在學校還沒有結婚時,色彩曾是非常鮮豔亮麗的。  但於1977結婚前後,李錦繡的繪畫開始出現非常獨特的個人風格,都是在描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諸如《都市人影》1976、《對影》1977、《家族因緣》1976、《旅遊》1977、《無言》1976、《影之人》1977,不管是出於水墨、油彩、水彩,顏色都相當單調灰暗,人與人之間呈現著各自疏離的寂寞存在,臉上五官都刻意被抹去,彷彿是沒有身份的幽靈。 李錦繡「合照」  李錦繡「婚禮」  李錦繡「伉儷」  只有《同學六人行》1977,在灰黑底上打下藍紫與綠的鮮豔顏色,同學們的臉依稀可辨,尤其是嘴角,很清晰的流露著快樂的笑,這是她繪畫中難得見到的快樂,可看出李錦繡對她同學的感情。  在李錦繡預備赴巴黎前的作品《家族系列》1981-82,一如《婚禮》1978與《合照》1982,人更消逝進單調色彩中,成為白色的或黑色的透明影子,《家族系列》,還有很多黑色質感很重的橢圓巨點,壓在這些透明影子上,巨點下的血紅,給人的感覺竟像是壓出血來。儘管是處理最親密的人際關係,家族與血緣,李錦繡從不曾放過一點溫暖在其中,因此,用「虛幻」來提綱挈領這個時期的比喻,是很恰當的。 李錦繡的「家族姻緣」1976  李錦繡的「家族」1981  李錦繡的畫給我的感覺是要讓人窒息的壓迫感,非常不快樂的主題與色彩。她畫她自己也是如此。  《自畫像》(1976),呈現著的是扭曲變形的臉,它立刻讓我想到英國畫家法蘭西斯•培根的作品,他正是用著扭曲、變形,呈現人的心靈陰暗意識。1977的自畫像,一如《同學六人行》,有了灰黑暗底之上的紫與綠,但色彩並沒有改變陰霾,她的臉是憂愁的、身影是寂寞的。 以李錦繡這時期所有繪出的人際,與她所繪出的自我相較,儘管自畫像呈現著憂愁寂寞與扭曲,但這自我表達其實很強烈,看畫的人可以充分感受的到,在一切虛幻如幽靈、影子的人際關係中,李錦繡以其獨特的方式強烈的存在著、並表達著自我,她的自我非常明顯的浮出於她的周遭世界之上。 匆匆的光影  王素峰為李錦繡巴黎時期「匆匆的光影」製作的裝置藝術。 從台灣南部到巴黎都會,李錦繡到巴黎後創作風格的徹底轉變與強烈的實驗性,以她的才華,是絕對可以預期的。而巴黎時期(1983-86)與返國後風格的斷裂(1987-91),也是一個充滿創造力、絕不因襲模仿的畫家必然會發生的國際與本土的斷裂。 但這兩個時期,她所關注的「空間」,我發現跟她早期、晚期作品中,「探詢與表達自我」這個主題,繼續交合成為一組彼此密切關連的雙重奏,在日後代表自我的空板凳繪畫主題中,充分表現出來。 巴黎時期的李錦繡,著重研究的空間,是真實與非真實糾纏交錯的虛幻宇宙,她以透明或半透明材料製造出多度空間,眼神可在多度空間中穿透出入,幾乎能使不同空間完全聯繫,並賦予周遭光影變化的效果。她說,她意圖開闊原本有限的空間,創造出「虛幻的宇宙」。 
 
  她在巴黎時期仍舊有多幅自畫像,但她呈現出來的自我,儘管有巴黎時期的抽象形式,但那些自畫像卻呈現著完整自信、一點都不扭曲、甚至略帶幽默的風格,那是她所有繪畫時期,將自我表達的最飽滿的時期。 『自』覺的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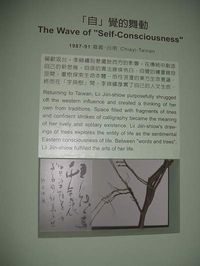 王素峰為李錦繡返台後「『自』覺的舞動」製作的裝置藝術。 回到台灣後,李錦繡對空間的探索,從多度空間的真實與非真實,轉而變成一棵樹樹枝向上向外伸展,對空間產生的變化感。這種空間探索,類似畫家蒙特里安透過樹對宇宙的探索,只是,李錦繡放棄理性分析的西方精神,透過她精湛的書法藝術的筆觸,表現感性浪漫的生命力。李錦繡說,「每棵樹都像個字。」 李錦繡像畫一般的書法。  李錦繡這幅畫,是透過繪出玻璃帷幕,產生多重空間,並在這些空間中繪出右側巨樹攀升向上,左側轟然崩裂癱倒的戲劇性效果。  每棵樹都像個字。  充滿感性浪漫的生命力。  李錦繡「生命」  1992年的《融》,我將之視為過渡到「竹板凳繪畫時期」(1992-95)的作品。畫面構圖切割為三,左側與右側,都是四處伸展、自由奔放、充滿生命力的樹枝,隱隱可看到濃密有力的樹枝後面,是有著門框的建築,畫面中央,建築被白色顏料塗去,(這種塗去法,在李錦繡後來的作品中,成為蠻重要的一種繪畫方法。)只剩下門框,門框內,一個女人坐在長凳上,五官難辨、面容模糊。 以下作品「融」置中,「融」的左側,是充滿生命力的樹下,畫家置身自然中作畫,「融」的右側,是充滿生命力的樹下,一對情侶款款深情的談心。左右這兩幅,更對襯出「融」這幅作品的過渡性,李錦繡即將把靜觀繪畫的對象,由大自然充滿生命力的樹,轉向室內觸目所及的物件。   自在的自『在』  王素峰的裝置藝術「自在的自『在』」。  就是1992年,李錦繡繪畫風格再度轉變,我將之稱為「竹板凳繪畫時期」。這段時期,李錦繡以穿黃脫鞋的腳、和一張竹板凳,表達自我,而這種表達,是充滿高度的銓釋空間的。
就是1992年,李錦繡繪畫風格再度轉變,我將之稱為「竹板凳繪畫時期」。這段時期,李錦繡以穿黃脫鞋的腳、和一張竹板凳,表達自我,而這種表達,是充滿高度的銓釋空間的。1992以後,李錦繡的繪畫作品風格再度轉變,樹的主題不見了,彷彿《融》這幅畫作最中央的門框內景,成為主要的觀看對象,室外那一切充滿生命力、爆發的樹枝,全消失無形。 1992年《進行中的自畫像》,是李錦繡在風格轉變時畫的自己,她畫自己正蹲在地上,處理尚未完稿的自畫像,因此畫中呈現兩個自我,其中一個,蹲在地上,畫面下方是張竹板凳,這個自我的面容依循她經常使用的肖像畫法,把臉擦塗過,模糊著五官,另一個自我,是在畫中的畫裡,輕輕淡淡的勾勒,彷彿褪進畫布中,即將隱形;饒有深意的是,畫中的畫布像個鎖住自畫像的閉鎖空間,甚至像個棺木。這幅畫具有很強的、對日後風格的暗示。  李錦繡1992年後所畫的室內,仍舊是空間的探索,但所有的空間都充滿物件,是被佔滿的空間。黃海鳴研究李錦繡這時期的作品說:「在《有壺的圖像》這件作品中,錦繡一件件的將廚房中一切繁瑣的事物抹除,只剩下不完全的輪廓,唯一留下來的就是中央那把茶壺,這種更加人工化以及觀念化的行為,更能凸顯日常生活以及居家空間所給他的某種負擔。」(黃海鳴《李錦繡的在家「任遨遊」》) 李錦繡「書房一隅」1992(右)  李錦繡「風雲際會」1993  當我看她所繪的《觸目所及》1993,各種各樣的家庭物件中,隱著小小一張竹凳,以及她穿著拖鞋的一隻腳,無法不讓人感覺,她被家庭需要淹沒到只剩下竹凳與雙腳,企圖吶喊些什麼。 李錦繡「觸目所及」  這時期仍舊是空間探索與自我表達的雙重唱,隨著觀看家居空間被生活種種必須物件、與藝術收藏佔滿,變得凌亂不堪,李錦繡的自我表達,也出現她最著名也最重要的,代表自我的竹板凳、與雙腳。這時期她出現於畫中,總是家居空間角落自己的一雙腿與腳丫子,她的臉與上身是完全在畫框外不被看見的,要不,就是她常坐著的竹板凳,她用竹板凳代表自己,無言的盤據充滿物件的凌亂房間的一角。     黃步青提到和李錦繡論及婚嫁時,席德進老師曾表示不贊成,原因是,他對李錦繡的創作才華非常肯定,他曾在李錦繡班上當眾說:「你們班上只有一個畫家,就是李錦繡。」因此,他對李錦繡與黃步青是冀予一樣的厚望,而婚姻,勢必導致其中一人得犧牲,當然最有可能是女人,席老師出於關切,十分不忍心。當時,黃步青當場允諾,他會一輩子支持錦繡的創作,席老師方才肯參加他倆的婚禮。 可是日後跟李錦繡一齊受教李仲生門下的藝友程武昌說:「李錦繡相當有才氣,不知為何在藝術活動上少下功夫,也許我們的時代是男女有別,藝術創作這件事也大都重男輕女。」 王素峰在《竹凳移動去——看李錦繡的藝術》一文中談到李錦繡的竹板凳時期也說:「熟識李錦繡的人都說她成天料理家務(買菜、料理三餐、洗衣、拖地....),兼課、教兒童畫,還得幫黃步青作裝置藝術,可以說裡外忙得團團轉。」 李錦繡的先生因為從事裝置藝術,因此很喜歡從外頭撿一大堆可能可以被使用的物件回來,堆滿了家中所有的空間,在這時期,李錦繡甚至沒有專屬於自己、可以讓自己安靜思考作畫的空間,直到過世前三年才在外面有了自己的「李錦繡工作室」。 有兩幅畫,暗示這樣的生活中,李錦繡與丈夫之間的關係。這兩幅畫都很有意圖的在透過作品說話。 李錦繡「居家」1992  另一幅《觀自在之三》(我和....?1995),看了也是讓人有不可言喻的複雜心境,畫中是她的雙腿雙腳,對面是另一人的雙腿,兩人都沒有出現上半身與臉。對面那人顯然是丈夫黃步青,但只有雙腿雙腳的對坐,特別呈現出一種不該有的距離與沈默。  被空間佔滿後的雙腳與竹凳,沒有上半身的自我,無法不叫人感覺,李錦繡充滿透過繪畫反應她這時期感受到的、自我的缺席。 自我缺席的竹板凳時期,於2002年告終。 完璧的堅持  王素峰為李錦繡生命最後時期創作的裝置藝術。 2002年,李錦繡以油蠟筆畫了一幅自畫像,她舒適的坐在有靠背的大椅子上,雙腳翹在另一張椅子上,雖然臉上一貫以色彩塗抹弄得有些模糊,但仍看得出臉上的自信神采,畫面最下方,出現一雙她竹板凳時期的腳丫子,被畫於靠著椅子的黑板上,彷彿是以在現完整的自我,省思過去那上半身不曾露面的竹板凳時期。 就是在這一年,李錦繡發現自己罹患癌症末期。  2002年,李錦繡的繪畫,色彩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2002年所繪的《容和、相待、彩虹曲》,一看畫就覺得那真的是另一個不同於之前家居的世界,色調不僅柔和、而且用了非常多亮麗的暖色,顏色協調互補,沒有任何衝突感,空間也不再被物件擠滿,整齊、潔淨、清爽,還出現綠色盆哉。在這幅畫中,仍只出現她的下半身,但兩隻腳,已非常明顯的伸進畫面至少三分之一的空間,此外,還出現了雙手,雙手正在悠閒的作畫。整幅畫呈現的色彩、空間與悠閒作畫的雙手、舒適伸展的雙腳,都讓人分外感覺這幅畫已表達了,李錦繡期待的空間感與自我感,都讓她十分的滿意。 唯有左側《容和》在溫柔亮麗的色彩中,可以看見一男一女仍維持著不對話的疏離關係,這意味了,透過色彩表達出來的心境轉變,應當跟已然疏離惡化的夫妻互動沒有關係,李錦繡心境轉變,應另有原因。   《容和、相待、彩虹曲》這種空間、色彩、自我在畫中的呈現,出現這麼大的蛻變,跟竹板凳時期,一看即知分屬不同繪畫時期,這應當是跟李錦繡2001年春天成立了工作室有關,那是以她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是她自己的空間。畫中的輕鬆愉快,充分暴露著李錦繡一直以來的渴望:她需要有自己的作畫空間,這空間攸關她是否能擁有完整的自我。 自此,李錦繡空間與自我的雙重奏,終於合而為一。當我追溯李錦繡年表,愕然發現李錦繡畫《容和、相待、彩虹曲》這系列畫時,已經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末期,我更加受到了震撼。這似否意味,李錦繡其實不懼怕病痛與死亡,她生命中色彩的黯淡,苦痛更 多是來自家族婚姻親密關係的虛幻感、自我的缺席、空間被丈夫物件塞滿、跟丈夫之間沈默的無言? 2003年,李錦繡畫下她的父親、母親、丈夫與弟媳,題為《安寧注視》,筆觸與色彩都充滿強烈的情感,像是要畫下永恆的記憶,而畫中的丈夫黃步青,色彩仍充滿著強烈的詮釋性,比對之下,可以看出來李錦繡對父母、與對丈夫,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感,李錦繡臨死之際畫下的丈夫,不再背對著她沈默無語,而是一種讓人倍感壓力的直視。   李錦繡的心靈世界絕不只是陰暗不快樂的,我們看她為幼稚園孩子們所做的創作,看她有自己畫室之後呈現的色彩,我們知道她心靈中有童稚、有明朗的春天,但是,這些似乎沒有呈現於她婚姻家居的繪畫中。 李錦繡為幼稚園的創作。     2003年十月,李錦繡病逝。女性主義批評家Elaone Marks說:「何處有壓抑,何處就有女性。」在壓抑論的基礎下,發現女性在傳統中呈現出來的沈默與缺席,其實有其隱含的不可知性與多元性,這些沈默與缺席,頻頻在問:「我是誰?我在和誰說話?」 仔細透過藝術作品聆聽李錦繡的心靈世界,我同意藝評家黃海鳴在《李錦繡的在家任遨遊》一文中所說的:「你相信,有些話是無法對身邊最親的人說,卻可以透過藝術的手法對能夠傾聽的感官訴說?」 李錦繡畫中所述說的,關於空間與自我的探索表達,到最後我們發現,她終於能在徹底屬於自己的空間中,完整的表達自我溫馨亮麗的色彩,而這份溫馨亮麗卻來自癌症末期、完全與婚姻與丈夫無關的臨終安寧,心中實在為李錦繡這短暫一生抽痛不已。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李錦繡巴黎剛回來,透過書法筆觸繪出的樹的生命力,我只能用自己心靈深處的誠摯回覆她:我會更加善待、珍惜我這份自在舒展的生命力,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份福氣。 後記:李錦繡紀念展的觀後感 我不是專業專職的藝評家,我只是透過媒體之便,經常跟人分享美好的藝術,我很容易被藝術感動,我也一向認為,好的藝術一旦被人感受被人理解,它可以呈現的心靈世界,遠比言談深沈的多,站在這些藝術作品面前,既是沈默的聆聽、也是心靈深處的對話。第一次進「李錦繡紀念展」會場,已是台北市立美術館閉館時分,我只有一點時間看到這位畫家的最早期作品,感覺她的風格很類似英國畫家法蘭西斯•培根,而培根又是我非常不喜歡的畫風,因此我對李錦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但我當時已注意到她最早期風格的展覽室最尾端,正對著我,有一幅非常大幅的作品,風格截然不同,這在我心中激起一個問號。 第二次進美術館,時間夠多,我順應展覽空間的流線,進入李錦繡不同時期的作品,我發覺,漸漸的在我和她之間,彷彿有一扇門正在打開,我被引進入李錦繡的心靈世界,開始聆聽她的聲音。  幾間展覽室走完後,我被一個女人無法言說、卻從畫中充分表達出來的真實給震撼了,我離開後,她的畫仍在我腦海跟我說話,以致於我有一股衝動,想要好好介紹她的藝術作品。
幾間展覽室走完後,我被一個女人無法言說、卻從畫中充分表達出來的真實給震撼了,我離開後,她的畫仍在我腦海跟我說話,以致於我有一股衝動,想要好好介紹她的藝術作品。我認為李錦繡的作品,雖然很容易被以女性主義觀點討論,但她的作品絕不能只以女性主義角度來解讀,因為她的作品可能產生的多元詮釋,絕對要豐富很多。我想,成為一個女人之前,得先是成為一個人。 她的作品最震撼我的,是自我與空間的那股強烈的渴望。何以最具親密關係的家族與婚姻聯繫,是這麼的虛幻、不快樂?何以在1992到1993之間出現一股裂斷,大自然中樹木的生命力不見了,空間擁擠到被物件塞滿,自我表達也僅剩下腳與竹板凳?我更想探問的是,到底她筆下充滿爆破生命力的樹木、與空板凳,哪一種更在吶喊自我? 儘管我並不打算以女性主義角度,來解釋李錦繡藝術作品拋擲出來的問題,但我仍以文化觀察的角度,暫時借用女性主義批評家ElaoneMarks的理論,他說:「何處有壓抑,何處就有女性。」在壓抑論的基礎下,發現女性在傳統中呈現出來的沈默與缺席,其實有其隱含的不可知性與多元性,這些沈默與缺席,頻頻在問:「我是誰?我在和誰說話?」 空的竹板凳立刻讓我感受到的,就是壓抑,對空間與自我的探索表達,也是不停的在追問:「我是誰?我在和誰說話?」從她畫中丈夫背對她的身影,這個問題李錦繡不只在問自己、也是在問丈夫。  我從藝術中感受到的是,儘管李錦繡是傳統女性,但這詰問不只是女人對男人,更是藝術家對藝術家的詰問。一個擅長用藝術探詢表達自我的藝術家,看到她所居處的空間,全被另一個藝術家所有的物件所充滿,她作畫得用頂樓倉庫與車庫,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完整畫室,這更深的詰問可能是:「同樣都是藝術家,我的位置在哪裡?」
我從藝術中感受到的是,儘管李錦繡是傳統女性,但這詰問不只是女人對男人,更是藝術家對藝術家的詰問。一個擅長用藝術探詢表達自我的藝術家,看到她所居處的空間,全被另一個藝術家所有的物件所充滿,她作畫得用頂樓倉庫與車庫,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完整畫室,這更深的詰問可能是:「同樣都是藝術家,我的位置在哪裡?」黃步青曾談及他載李錦繡到公園畫樹,不過,從認識李錦繡的人們的追憶,都是看見李錦繡協助丈夫的裝置藝術創作,但對丈夫黃步青協助過李錦繡的創作,似乎不曾有印象。(另可參李錦繡紀念集中的李錦繡記事年表與所附照片)。從傳統觀點,旁觀者會稱羨夫唱婦隨,可是在看到李錦繡畫中空著的板凳、缺席的自我,卻又發現,李錦繡實在是個壓抑的、不快樂的女人,她並不滿足,她用缺席與沈默吶喊。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空板凳,比樹木的生命力,更震撼我。不管對象是男是女,若真正聆聽到壓抑的沈默與缺席,會聆聽到最多元、最讓人意外不可知的聲音。天可憐見,李錦繡若是沒有罹病過世,她有了自己的畫室後,可以透過藝術作品表達出來的多元與不可知,將會如何的豐富每一個熱愛藝術的心靈。對李錦繡終於有自己的畫室,走出溫和亮麗愉快的繪畫風格,卻突然癌症過世,我心抽痛不已。 我刻意將這篇感性主觀的文字,與帶點距離分析李錦繡畫作的另一篇文字分開(即拙作「李錦繡的「空竹凳」」,主要原因是,我覺得李錦繡的作品像是一本日記,把她這一生攤開在我們面前,置身於她的作品前,用心聆聽,很難不產生一種主觀的情感,即連我意圖帶著距離感來分析畫作,還是很難徹底的客觀,更何況這篇文字,又是我用情很深的回應。 因此,我真的很想聽聽其他喜好藝術的朋友,在看過李錦繡的作品後,有什麼心得、心情與感想。 譬如說,您對她巴黎時期的光影分析,以及回台灣後所畫的「樹」系列,感受到什麼?您對她早期的作品,與空竹板凳的想法,跟我有什麼不同?以及李錦繡最晚期作品,您有沒有就此看出,若她沒有過世,她可能會走出怎樣的畫風?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藝術創作更是充滿了自由度,很可能因著您的意見,使我跟您之間也出現彼此的聆聽與對話,引出我和你心靈中更多的多元與不可知,我想,李錦繡在天之靈,一定很安慰很快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