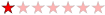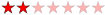還需要作點作者和時代研究的功課才完整些。
其實七等生許多年後寫了我愛黑眼珠續集,應該擺一起看的。
有些東西,想寫但是還沒辦法明白描述出來。這是我的瓶頸。:p
總之,先暫放。.....
------------------------------------------------------------------------------
是罪人或是超人?--讀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1939年生於苗栗通霄,幼時家貧,家中育有十兒,父母不得已將一稚女送養他人。十三歲時喪父。後考入台北師範學院藝術科就讀。求學時成績並不突出,行為倒引人側目,曾因為跳上餐桌抗議學校伙食欠佳而被冠為「特殊份子」遭退學,之後由老師作保方才復學。師範畢業後,懷秉著天真的理想至九份、萬里等偏遠學校教書,挫折屢受。二十三歲時入伍服役,是年,長兄玉明患肺病去世。二十五歲退役,返回萬里國小任教。一年後結婚,辭去教職,專職創作。
七等生的作品,擅長於在現實描述中穿插人物內心的獨白,透過一個情境,反應一種哲思之情。因為重視這種孤寂個人面對生命問題的思索,他作品中的角色往往令人感覺處於社會或團體邊緣,所做出的行為決定也跳脫甚至反抗一般人對於生活常理的認知,因而時常引發議論。
「我愛黑眼珠」就是七等生短篇小說中引發道德爭議極大的作品之一。主要在於七等生用在災難中捨棄被視為應當持守的夫妻關係,去拯救一個大雨落難的妓女,來表達他所謂「人類愛」以及「憐憫」的主題。而這樣的捨棄究竟是一種對人生的消極回應與道德意義淪喪?還是因為對苦難世界的極度憐憫能致使一個人願意捨棄個人意義,起而拯救他人?
<我愛黑眼珠>
故事起於一個下著傾盆大雨的下午。李龍第,一個在城市中無法被任何符號定義身份的普通男子,出門去赴他那挑起維持家庭活命責任的妻子之約。他在城市中移動,隨時採著思考的姿態,走進大雨和人群中。城市的人聲雜語在他眼前晃動,他看著這世界,也與世界隔離。
他原本是和晴子相約在戲院門口要一起看戲,戲開演了,晴子卻還沒有到。他轉而到晴子工作的特產店,晴子卻已先離開。雨水越積越多,找不到晴子,他在這座沒有防備而突然降臨災禍的城市失掉了尋找的目標。
水流終於成災,衝散城市原有的面貌,衝散城市的秩序,人們奔逃擁擠,拼命想要求得活命而顯露出不堪的人性。李龍第倚靠在角落石柱邊,為著眼前這一切思索和痛苦。
另一陣混亂中他救起了一個跌落水中虛弱的女子,背負她爬至屋頂避難,用妻子的雨衣包覆她。天亮之時他發現遍尋不到的妻就在對面屋頂,妻同時也看見呼喚他,李龍第卻決定摒棄過往的一切,將照顧懷裡這個生病的陌生女子視為當下自身唯一且重要的責任。他漠視妻的呼喚以及怒吼,將在雨衣裡原本預備好給妻的麵包給了自己眼前這個飢餓且軟弱的女人。
[color=blue]「你叫什麼名字?」「亞茲別。」李龍第脫口說出。
「那個女人說你是李龍第。」
「李龍第是她丈夫的名字,可是我叫亞茲別,不是她的丈夫。」[/color]
對面的妻從震驚、憤怒,到低下頭哀傷的細數往事,渴望丈夫的回應,而李龍第只是關注著一口口吞吃麵包的女子。這個城市裡的一名妓女。後來他才知道。但在這個當下,往事也不再重要。「[color=blue]為什麼人在每一個現在中不能企求新的生活意義呢?生命像一根燃燒的木柴,那一端的灰燼雖還具有木柴的外型,可是不堪撫觸,也不能重燃,唯有另一端是堅實和明亮的[/color]。」在此刻,李龍第和妓女不存在,存在的是亞茲別以及生病著的女子。
基於感激,女子仰身熱烈親吻李龍第,「我愛你,亞茲別。」對面的晴子憤怒的落水,被水流沖走,李龍第掉下眼淚,但沒有動作。水退去,他陪著女子走到火車站,把水災前原本買給晴子的一朵香花插在女人頭上,她戴著花,穿著雨衣,坐上回家的火車。
亞茲別又成為李龍第。他要回家好好休息,並且,在這龐大和雜亂的城市裡,尋回晴子。
<是罪人或是超人?>
這篇文章甫發表時爭議非常非常大,主要是若從男女感情和社會道德觀的問題切入,李龍第身為一個丈夫,怎麼可以這樣不顧自己的妻子,尤其前面他對妻子的依賴,到洪水來後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是很矛盾的。
李龍第(或者暗指作者七等生自己),因此被責備是冷漠而孤傲的社會邊緣人。七等生後來自己曾撰文辯解說,這篇文章要談的是「人類愛」和「憐憫」,並且舉了聖芳濟得道之例,表達『一個人某種思想人格之形成,除了第一要素他的「秉性」外,有他的醞釀期,和那重要的「使他突破的機遇」。』
對李龍第來說,突來的洪水也許就是這種機遇,把他將過去完全割離,得以以亞茲別的身份出現。落難的妓女在那個當下成為他的使命,他因此對於對岸的晴子會有如下的心理陳述:
[color=blue]「妳說我背叛了我們我們的關係,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中,我們如何再接密我們的關係呢?唯一引起你憤怒的不在我的反叛,而是你內心的嫉妒,不甘往日的權益突然被另一個人取代。至於我,我必須選擇,在現況中選擇我必須負起我做人的條件,我不是掛名來這個世上獲取利益的,我需負起一件使我感到存在的榮耀之責任。.....」[/color]
此刻的我與過去的我已完全無關,在此當下,亞茲別的使命是照顧這個女子。
然而,即使如此,不論象徵或是寫實,李龍第這個角色所展現出來的東方社會的憐憫,都與聖芳濟這樣的意象有文化本質上的差異。這不在於外顯行為的合理與否,更是在內在價值觀的截然不同。西方的罪感文化,首先在自覺體悟自己本身的能力有限,是一個不完全的罪人,而這個罪無法透過自己解決,必須尋求一個「他者」介入。所謂的「憐憫」,是一種「明白我們都是同等的罪人,需要同等的救贖,我並不比任何人更高一等」的心情,同時,必定經歷與「他者」對話,在善跟惡的人性中掙扎的過程。最終個人的行為,是在同等力度的兩方拉扯下的一種選擇。
但是李龍第卻幾乎沒有這樣的掙扎,文本裡,他內心最深處幾乎都是一種冷然的理性鎮定。面對大水時,他的中心思索仍是個人並且超然的
[color=blue]「在這個自然界,死亡一事是最不足道的;人類的痛楚於這冷酷的自然界何所傷害呢?面對這不能抗力的自然的破壞,人類自己堅信與依持的價值如何恆在呢?
他慶幸自己在往日所建立的曖昧的信念現在卻能夠具體地幫助他面對可怕的侵掠而不畏懼,要他在那時力爭著霸佔一些權力和思欲,現在如何能忍受的住他們被自然的威力掃蕩而去呢?那些想搶回財物或看見平日忠順呼喚的人現在為了逃命不再回來而悲喪的人們,現在不是都絕望跌落在水中嗎?他們的雙眼絕望地看著他們漂流和亡命而去,舉出他們的雙臂,好像傷心地與他們告別。
人的存在便是在現在中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在這樣的境況中,我能首先辨識自己,選擇自己和愛我自己嗎?」[/color]
李龍第並不在那些為了生存而逃命的人群之中,環境與衝擊不會打擊他的任何信念,甚至,他對於死亡也無所畏懼。當他救起生病的妓女,對於對岸出現的晴子,他認為「[color=blue]我在我的信念之下,只佇立著等候環境的變遷,要是向那些悲觀而靜靜像石頭坐立的人們一樣,或嘲笑時事,喜悅整個世界都處在危難中,像那些無情的樂觀主義者一樣,我就喪失了我的存在[/color]。」
由此看來,李龍第的形象所傳達的愛與憐憫之主題,要說是聖芳濟式對於人世苦難靈魂的屈身悲憫,因而不顧責難,產生行動,或者更傾向尼采式的超人形象,「上帝已死,人要成為超人,用自我意志力克服虛無」。他的意志何等堅強,幾乎不被打倒的。面對危難的處境,他斥責晴子的嫉妒,因為晴子應該體認到他們彼此之間的鴻溝,不該不甘過往的權益被另一個人取代,這是晴子的軟弱。而亞茲別,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人,可以拋棄一切過往,不受過去任何牽絆,內心不經任何掙扎,完成這件「使他感到存在的榮耀之責任」。
然而人性的軟弱難道不真實?若說拯救落難女子是種堅定信念的實現,那麼導致晴子的落水難道就是為實現信念而不得不的犧牲?他對落水的晴子內心默默的安慰是「[color=blue]現在你看不到我了,你的內心會獲得平靜。我希望你還活著[/color]。」是理性?是冷漠?是對信念的堅持?單單同是作為一個人,晴子之輩何辜?她理應如此?那麼,這是否也成為「欲善成惡」的弔詭?李龍第並沒有錯,卻不代表他所做的行為就會導致善的結果。對那城市中的妓女來說,他是善的,對晴子來說,
他所做的卻足以毀滅。
若是談憐憫,談存在,李龍第究竟是罪人?抑或超人?然而翻遍文本的思索與脈絡,我似乎仍是在他的身上看到超人的悲劇英雄形象,比體悟承認自我人性的軟弱,轉而祈求救贖的罪人,要多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