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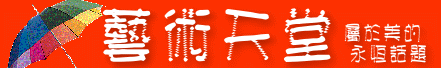 |
|
|
|
|
陳韻琳  不安的謬思 基里訶 基里訶這幅畫引起藝術界的騷動不安。 不知多少詩人、藝術家,的確將謬思的沈靜凝思類比為愛情的神聖,將謬思的突然生發帶出來的狂喜,類比為愛戀的激情。當然,謬思絕不只是如此。僅只在愛情中尋找謬思的藝術家,終將成為玩情不恭的絕情人。這在藝術史上,已不勝枚舉。難怪希特勒瘋狂愛上這幅畫。這樣的輕盈女子,一樣可以模擬為政治激情下的謬思。 「不安的謬思」不僅使當時的藝術界不安,也使當時的觀畫者不安。 觀畫者心中的某根弦被觸動了。因為每個人的人生,都是舞臺上的木偶。謬思在哪?靈魂在那?如何找到心靈深處的沈靜?如何走下舞臺框框,在最真實的生命與生活中活出最想望的自己?對白、劇情、與跟我同演人生戲碼的人在那裡?他們有沒有謬思呢?萬一其他人仍心甘情願作著木偶,走下框框尋回靈魂的人,會是何等寂寞孤單呢? 馬庫色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剖析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社會,其實跟極權社會中的人一樣,會變成「單向度的人」缺乏一種超越性的思考。極權社會的單向度,是因為容不下異己的聲音,資本主義社會的單向度,是因為被物化社會收編。 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個浪漫故事嗎?—一個男人偶遇一個女子,在數度偶發事件中,最後結束了生命。浪漫唯美嗎?其實不是!米蘭昆德拉在說著當人沒有「生命之最重」,只能隨「生命之輕」起舞,最後,一切生命之輕,都會成為「不可承受」的沈重。這是一種悲涼。生不知其重,死不知其意。因為人人都活的「媚俗」,人云一云。 今日,你我發出聲音。這是生命之輕還是生命之重?靈魂的向度、沈靜的凝思在那裡?是置於舞臺四周空曠無人的舞臺上?還是更糟,你我在媚俗的生命圖景中,根本走不出畫地圈限的框框? 安靜的四處凝望,尋找向你我微笑的謬思。找回靈魂的渴望、找回沈澱後的深度思想、找回靈魂深處的啟動機。因為你我都可以不是「不安的謬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