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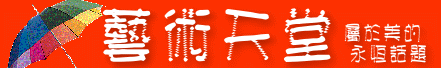 |
|
|
|
|
陳韻琳  偉大的形而上學者 基里訶 當基里訶繪這幅圖,又定此標題時,已經蘊含一種反諷。 觀畫者提問時,就對「偉大的形而上」提出反諷。 哲學的形而上之探究,變成許許多多瑣碎的問題:「為什麼毛毯不掉下來?」或一針見血的大哉問:「哲學,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幅畫的主角是「偉大的形而上」這些置於廣場中央的量尺物件?它僅只諷刺哲學之形而上??這是我一再問自己的問題。 我的e-mail信箱是個寶庫。他們不直接在版上回應議題,他們私下跟我討論,因為他們想觸碰我的心靈,也想讓我觸碰他們的。就是這種隱密的交流,讓我感受我與他們的同一:倉促流逝的時光下,永恆的孤寂靈魂。沒有人是不孤寂的,因為每個人的心靈都是如此獨特,都在成長之路遍滿傷痕,都冀望著某些立即的答案,最終又發現這些答案跟永恆的孤寂無關。 有時後BBS洩漏著一個訊息:大家用議題討論,其實是在遮掩自己。一個一個議題,你來我往間,隱藏自己不敢面對的自我。議題越是偉大,可能心靈越是孤寂。越是強悍,其實內心可能越是無助。自承強者,比弱者在內心深處有更多的哭泣。你得到心靈的安息了嗎? 信仰是一生之事。面對著向我誠實,也冀望我對他誠實的人,我對很多立即的困難給予立即的建議,然後,我只能說:「人生並不容易。立即的答案不是永遠的答案。」生命自在奔流,我在我的人生秘密中隱藏關乎信仰的訊息,這些訊息不是知識,它需要用生命走過,旅途終站才見分曉,那些事,容許我不用談論的,我願意我這一生是一台戲演給你看,因為這比現在跟你談論,是更加的誠實。 在我剛強背後顯露的靈魂孤寂,在我孤寂背後顯露上帝之愛的巨大能量,這只能用我一生攤平給你看,言語,是何其的有限。 這就是為什麼我從來沒有把偉大當成主角。偉大,最終總會淪落成沒有靈魂的量尺。所有的學說、意識型態、學科、或英雄人物,何時變成偉大,何時就慢慢走向量尺的墮落。 你曾從這一切偉大的背後,看到孤寂的靈魂?你曾遇見過那個在時光流逝中孤獨的身影?你曾發現那人是你,那人是我?何時,我們可以在畫面角落、不再是中央,我們可以在孤寂中而不是在偉大中誠實的相遇呢?何時,我們可以丟掉不居是什麼的遮蔽隱藏,認真的面對自我、理解自我呢?? 我聽到時光在光影中流逝的聲音。我看見生命本身正在透露不居是什麼的信仰本質。我聆聽靈魂深處的聲音,那真正關心孤寂靈魂的人,也聽的見我的聲音。 巨幅畫面上的巍峨量尺,我看到的是光影下渺小孤獨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