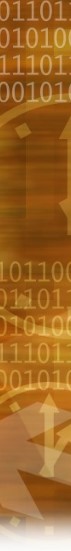


作為更新中國文化的基督教信仰 |
蘇友瑞 |
|
信仰與社會的互動 我一向的社會、文化治學態度是:按照韋伯的「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精 神」的社會學研究方式看來,個人盡其所能的「理性」,是無法處理與解決 「價值」的問題。然而,一個社會要從傳統更新成現代,面臨的正是「價值 系統」上的革命,這種革命無法以任何理性原則來更新。因此韋伯假設,一 個文化的宗教精神可以部份解釋該文化的基本價值系統,然後,隨著宗教精 神的改變,文化系統跟著改變;這種改變是因為社會變遷中需要某種原先「 傳統」裡沒有的精神,又因為「傳統」無法直接產生這種精神,因此透過宗 教精神的更新,該文化把「傳統」中某些可能的素材,跟著宗教的更新,加 上時代的塑造,從而產生符合現代社會所需的「全新價值」,這種歷程在韋 伯稱之為『創造的轉化』。 在韋伯的研究中,他觀察到「傳統」的這種精神:『原先我每天八小時 賺八仟元,現在老闆提高成每小時兩仟元,那麼我只要工作四小時賺到原先 的八仟元就夠了』,這是傳統經驗理念上『知足常樂』的精神。這種精神與 資本主義社會所需要的『今天我只要賺了錢,就要把用剩的錢繼續投資,一 直投資到無錢可投資為止。』這種『對經濟的獻身精神』是衝突的,由於韋 伯發現代表基督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喀爾文派教義成功的轉化基督徒面對『社 會實踐』的問題從『求屬靈生活中修行』變成『求現實生活中榮耀上帝』, 因此,基督教精神成為現代化社會轉變的重要因素。 這種從人類思想、價值系統來研究社會行為的研究方法,是社會學史上 偉大的典範。日後韋伯用相同方法形成一套『宗教社會學』研究史料,說明 了他這種方法的成就。
今天,中國文化(包括台灣、大陸、華人文化中心的任何地區)所面臨
的是什麼問題呢?
佛教結合儒道,帶出的「個人修行」觀 我的生活中常常體會到「社會實踐」與「個人修行」的嚴重衝突,在許 多情況下,我強烈的感受到:「我們發善心,不一定會為善」。很可能在某 種社會發展的需要上,我們不得不為惡,為惡反而可以使大範圍的社會成善。 在這樣的觀點下,我常常經驗到佛教是一個過份強調「個人修行」的宗 教,因為我們常常看到他們強調「人心的美好」可以決定「社會的安樂」, 這種認為「社會的良善」可以化約成「個人美好的修行」之思想,不但是傳 統儒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考方 式,在中國的佛教界更是主要的思潮(當然還是有例外,例如尊重社會運動 的釋昭慧法師)。這種思考方式,與基督教精神是非常不同的。 以政治上的「抗爭」事件為例,「抗爭」是不道德的嗎?今天任何示威 遊行,一定、也絕對會干擾到很多人,至少會干擾到交通的不便,甚至於常 常遵守社會心理學上的「去個人化」定律而造成流血衝突。毫無疑問的,進 行抗爭,一定會強烈違反「個人修行」。 問題是,在許多社會現實情況而論,當政府施政能力有問題、對於社會 上的需要不能立即回應時,「抗爭」往往是最有效的手段。以老國代退職而 論,這是政府由於自己的法令綁死自己,造成能要求老國代退職的人只有老 國代自己;因此,如果人民對此不滿,卻完全沒有任何合理合法的方式可以 進行。這時候,抗爭的出現不但人民的心聲,甚至還是幫了政府一個大忙─ 體制內的法令錯誤,唯有體制外抗爭才能找到解決方法。在這種情況下,沒 錯,抗爭是一個個人修行有缺失的行為,但是,這些人放棄自己的修行,大 多數人所認的正義─老國代應該退職─卻得到解決。這時候,再以個人修行 的角度批判別人上街頭所造成的問題,豈不是平白享受別人抗爭的成果,卻 自命清高的指責盡心力的人? 當然了,抗爭所造成的個人修行缺失是一定存在的,這是無法否認的事 實。然而,如果因此拒絕進行抗爭,每個人都是這種為了個人修行而不做事 的人,那麼誰來進行社會實踐?換句話說,這裡面臨了「個人修行」與「社 會實踐」不能同時兼顧的兩難,就算個人選擇退隱、逃避,一樣是社會實踐 的缺席者,也就是無形中幫助目前社會不合理罪惡的結構共犯。事實上,採 取為了個人修行而不做事、甚至自命清高的隨便批評出來做事者的態度成為 社會主要思潮,幾乎是我們目前社會最大的問題。 以上的例子,充分表現「個人修行」與「社會實踐」不可相互化約的事 實;我們平常所謂的「善」,往往不過是從個人修行去定義,這就常常鬧出 「個人發心為善,結果對社會而言成惡」的可悲現象。 佛教教義不利於社會實踐 我對現代台灣的佛教界之觀察也就在此。目前佛教徒的宗教生活中顯然 極為強調「個人修行」而不傾向「社會實踐」。若要說慈濟功德會,我會認 為那是一個最標準的『以「個人修行」的態度進行社會實踐』之範例,雖然 看起來像積極為社會做善事,但本質是一種「藉行功德來達成個人修行的目 的」,這種精神與基督徒──例如長老教會獻身政治改革與山地服務──完 全不同。長老教會的社會實踐是「以社會工作為最高目的,亦即為了榮耀上 帝」。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工作下,慈濟會要求他們的社會工作『不可沾染政 治』,為什麼不可?因為沾染了政治,個人修行就不再完美了。而長老教會 為了實踐社會良善,可以抗爭,可以一群牧師親自上街頭對抗,因為實踐一 種社會公義才是最高的目的,個人因為進行這種行動而不完美,便祈求完美 全能的神來憐憫人的軟弱。
所以我對國內幾個重要的佛教傳媒的印象就是,他們儘可能主張大家不
要去沾染政治問題,因為那是「不清淨的」;一但他們一談到政治問題,多
的是幫國民黨指控與咀咒民進黨是禍國殃民的亂黨。當然他們有權力這樣子
批評政治改革者,因為政治改革的初期,往往不得不借助一些非道德、傷害
修行的行動或手段──例如街頭抗爭,如果完全不理會這種行為的「社會意
義」,單單著重在這種行動伴隨的情緒衝動、妨害交通社會秩序等等不良的
道德修行,那麼這些政治改革者當然是十惡不赦的罪人了。結果,看不到這
種「社會意義」,而只知道用「個人修行」來進行批判,最後就是淪落成執
政黨的共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嚴重缺席甚至成為可悲的反面教材,這是
令人感嘆不己的。
以實踐經歷上帝的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的思想是,人類承認了自己的罪──在我的理解,是人類承認自 己永遠不完美,永遠不能成為神;然後努力去實踐基督的榮耀,不求自身做 的能達到無比的完美,因為有基督的血在承擔我們的罪惡。 這樣的思想,很容易可以使人在「個人修行」與「社會實踐」上的兩難 中解脫,因為這思想應許了人類可以不完美,而由一大能者來原諒這一切。 如果「個人修行」與「社會實踐」兩難的問題之答案若是無解,那麼對一個 可以原諒我們基於「人之有限」而犯罪的創造者負責,反而能使社會形成較 好的互動。例如說,重視「個人修行」與重視「社會實踐」的人皆可以平等 的對上帝負責,對個人而言兩種態度皆不完美,但對社會整體而言卻是整體 的良善。因此個人可以自由選擇他要重視那一方面,並不會有任任道德壓力 會信仰教條要求他一定只能重視個人修行或只能重視社會實踐。如此,我們 的社會才有可能現代化。 因此,從社會實踐的觀點,當面臨了強烈的社會不公義而起身抗爭的社 會改革者,為什麼許多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會不會是解決了他們心中「個 人修行與社會實踐」的兩難,透過實踐,使他們更經歷了上帝? 對我而言,這正是我認為必須用基督教信仰來更新中國文化的重要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