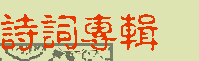|
 |
|
|
|
|
|
(一)明月
東坡詞中常有月,是明是缺,往往都有著多樣的意涵,人 月之間,總是有說不盡的轇轕。一輪明或者不明、圓或者不圓 的月,照李白,照東坡,照楊喚,照我。照東坡的月反射出怎 樣的光芒呢?先從月意象最豐富的〈水調歌頭〉看起吧: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一起首就是一個「天問」,「明月幾時有?」什麼時候開 始有月亮的呢?這就挑起了生命無解的根源問題,而這樣的問 題的出現,往往也就是一番尋索的開始。問「明月幾時有」在 我看來,等於是問「生命究竟是什麼?」也暗藏了許多相生的 問題,就開啟了全篇。之所以將「明月幾時有」這樣的問題「 把酒問青天」,是以月為昔在、今在、往後仍在之物,作為一 個宇宙的律、或者一條生命長流的象徵。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承上啟下,帶出仙境與人 間的對照,字面上看來,是說想到月(天上宮闕)之不受時間 限制(今夕是何年),當下情感上的反應是「欲乘風歸去」, 但在多想一層,「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這一方面可 以將「瓊樓玉宇」看成是一種完全超脫世俗、抽離於人情物外 的「仙境」,東坡否定了,他沒有要跳出生命長河之外,他是 「情之所鍾」之輩,不勝「太上忘情」之寒,不如在人間「起 舞弄清影」;另一方面,或者可以扣到之前的生命難題,當他 更深地迫近自己、反視生命,生命本身無解的情緒使他「恐」 且「寒」,像〈後赤壁賦〉中「凜乎其不可留也」的感受一般。
下片,月又變成了一個如影隨形的、總是以它的圓照人事 之缺的形象,「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無所不在的月光 照的是他無所遁逃的情緒,人與月開始有密切的對照關係,「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是強烈的反襯,襯出無情天地 中的有情人、不變的明月下擾動的人情物事。
之後又作翻轉,將人與月連結了起來:「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人長久」「共嬋娟」。原本以月反襯人生 的短暫與缺憾,是很深刻的情感流露,然後作了一個哲理的反 省:月也有陰晴圓缺,並不影響月的本質;人的悲歡離合,也 不改變生命的本質。如此明月與人生可以相互應和起來。
最後,再回到情感層面,以月為聯繫兩地有情人的媒介, 共一月,情相連,「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但願人情長 久,作為生命不變的本質之一,便可以超越悲歡離合、陰晴圓 缺。
大約可以歸納出,月在哲思上,是作為東坡「變與不變」 的辯證,在情感上,常襯出人事的缺憾與蒼涼。〈江城子〉最 末:「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一片無限淒冷的 場景。蘇軾作〈水調歌頭〉「兼懷子由」,兩人雖受空間阻隔 ,仍一情相繫,能夠「千里共嬋娟」,但在〈江城子〉,他懷 念死去的妻子,與他共一「明月夜」的,只有「短松岡」,說 不盡的蒼涼在言外。
(二)古今
登臨懷古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大主題,也是人性的一 大主題。當人的自覺從自己擴大到歷史、古往今來之中, 再視自己的生命,因而產生對生命的另一番觀照。
懷古作品的產生,常常夾帶著作者本身際遇的困頓、 情感累積,而對時間特別敏感,然後登臨某一特別的地點 ,或為城樓、或為古戰場,見到某些週而復始的自然現象 ,從而發出一番詠懷。下面從〈永遇樂〉、〈念奴嬌〉( 赤壁懷古)、〈八聲甘州〉來看東坡詞中的古今情懷。
〈永遇樂〉 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
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
ㄓㄣˋ如三鼓,錚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
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古今如夢,和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
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歎。
東坡作此詞時年四十三歲,知徐州,人生已過半,經 歷幾翻波折,亦不知往後又將貶調何處,胸中的鬱悶在「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的夜裡顯得格外清醒,「天涯倦客 ,山終歸路,望斷故園心眼」道出他長期事與願違、「此 身非我有」的情感堆積,時空的困頓都凝聚在燕子樓中, 「樓」的本身,就是一個孤絕、封閉的意象空間,再加上 這是個有故事的樓,「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他在樓裡夢見盼盼,夢醒了,盼盼不再;他的夢固然 短暫虛幻,但是真實的盼盼也早已不在。
如果有一架攝影機,從燕子樓搭起時開拍,然後快轉, 便見盼盼來了、走了,東坡來了、走了,又有後人繼續的 來了、走了,燕子樓依舊,黃樓夜景也依舊。蘇東坡此夜 心中所見的,恐怕就是這樣的鏡頭吧。「空鎖樓中燕」, 鎖住的是不得歸故園的他
作〈永遇樂〉後十三年,東坡寫下了〈八聲甘州〉( 寄參寮子),時年已五十六,意境顯得更為超曠淡遠,仍 帶著一股悲慨的底流。〈八聲甘州〉上片:
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
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
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頭兩句就有種類似「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人生洞見,是比 「人生如夢」更深一層的觀照。從前是「古今如夢,何曾 夢覺」,這裡是「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從前道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此處但云「白首忘機」。關 於今古,已經思量的很夠,頭髮也早白光了。這是他貶杭 州後又被召回朝廷、將要離去時寫給參寮子的詞。回到朝 廷,應當算件好事,而東坡說自己「白首忘機」,是他一 向的心志(他不是計較功名得失之輩),也是他的感慨: 仍然不能以物喜,因為際遇總如潮來潮去,無所謂有情無 情。這樣的言語,不就是一份惻惻之心歷經了更長的年歲 而顯得更淡卻也更深幽的反映嗎?好像杜甫〈自京赴奉先 縣詠懷五百字〉中所言: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
杜甫自比葵藿,也鎖在自己向陽的天性裡。
東坡說:「不用思量今古」,因為正在思量的當兒今 者已古,從前為思量今古而華髮早生的自己也真的老了, 還剩下的是一些記憶:「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 翠煙霏」,一個知己:「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一 點心願:「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 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在潮聲中、餘暉下,顯 得格外感傷,正是:「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 音」。
陸機〈弔魏武帝文〉云:「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 不忘。」王羲之〈蘭亭集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悲夫!....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蘇東坡的 悲哀通常沒有表現的這麼強烈,有的時候他說:「但願人 長久,千里共嬋娟」,有的時候他乾脆「一尊還酹江月」 ,有的時候「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但我總感到有股共通 的底流埋藏在字裡行間,或者是一種空缺、一番掙扎,或 者思尋某種永恆的想望....。
(三)行走
人在行走的時候,眼有所見,耳有所聞,身有所感, 可以乘載許多思緒,營造出某種心靈狀態。而人在某種心 靈狀態之下,也常會走出去,此時眼之所見、耳之所聞、 身之所感便都成為其心靈狀態的外在投射,好像一個時間 的旅人走著生命的路。在東坡的詞裡,「行走」常是孤獨 的,是有所醒覺的,醒覺之後,是清冷的。
〈永遇樂〉上片: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
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
ㄓㄣ\如三鼓,錚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
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東坡夜宿燕子樓,夢見關盼盼,下片寫的世人生體悟和詠 歎,上片就先寫他醒來在小園裡行走,見到清新可愛的景 象,卻是「寂寞無人見」,是他一個人的感受,也許此刻 夢中餘韻猶在,然後「錚然一葉」將他驚醒,清醒後,被 茫茫的黑夜包圍。
〈卜算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
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同樣是夜,這首顯得更加淒冷。「缺月」就是他心境的投 影,在眾人都睡去的深夜唯有他一人還醒著,忽而有人影 閃過,卻是隻孤鴻,這隻縹緲的孤鴻便成了他漂泊生命的 化身,「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執著著他的悲 劇性格,在寂寞、寒冷的夜裡不斷地飛著,也是一種行走 ,成為一幅不安的心靈構象。
〈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是一回很不一樣的行走,是東坡對其一生行年至此的一 次深刻的反省和體悟。詞前序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 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以而遂晴。」這 就產生了一個對比:其他同行之人「皆狼狽」,東坡「獨 不覺」,那麼他覺的是什麼?驟雨之於他象徵什麼?他又 是如何回應驟雨驟晴呢?
在狂雨中,他「吟嘯且徐行」,穿林打葉之聲他聽到 了,但是心並不因之惶恐,反而在雨中的行走比尋常更能 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對自己生命狀態的意識,雨是突如 其來的,但是我可以決定要倉惶抑或徐行,決定步伐輕快 與否的也不是竹杖芒鞋或者馬,而是自己的心靈狀態。平 常我們在大雨中感到不適,或突然放晴、山頭灑來陽光煦 暖,想必是雀躍不已的,而東坡在雨中已經不為所動、同 共節奏而行,那麼放晴又如何呢?在大雨之中總有份豪情 :就算一生風風雨雨也不過如此,我也不怕!「一簑煙雨 任平生。」雨停,「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 相迎」清風吹來,又醒覺一次,感到「微冷」(這次只是 微冷,是淡淡的、冷靜的,不像〈卜算子〉那樣淒涼), 微暖的夕陽又「卻相迎」,這是出乎他的期待的,因為他 原本在風雨中能夠自適,就不是咬著牙在等待放晴,一旦 放晴,他馬上就悟到了晴雨交替的道理,生命的本質是不 變的,下一次風雨不知何時再至,那無所謂,主角是那個 不斷行走的人。
這大概是東坡的詞作中對人生的反省與洞見最深刻、 最有姿態、又最能情理相融的一首吧。讀完了「也無風雨 也無晴」,下一個問題不禁浮上心頭:那麼,行走的人將 往何處去?「歸去」,歸去何方?或者,這又回到了「明 月幾時有」的那個問題去了吧。
歡迎和我們聯絡:gospel@life.fhl.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