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蘇友瑞
透過改編電影上映的推波助瀾,這本早在三十年前由國語日報社出版的《獅王、女巫、魔衣櫥》(當時譯名為《魔衣櫥》)故事又再次成為流行話題。想當年雖深深迷上這個故事,但對於故事意涵的理解卻有點模模糊糊。一個精彩萬分的故事,往往承載著豐富的精神意涵;能感受到卻說不出來,這就喪失進一步深入交流的機會了。於是隨著年齡增長,雖然己經遠超過允許進入納尼亞的童稚歲月,卻深刻體會這個故事的人性處境存在著根本上的文化差異;因此,一個預備邁向中年的成人,重新回到納尼亞的心靈世界。
不過老實說,個人對電影改編後太過於『迪士尼化』不是很滿意;所以本文以原著小說和電影並重,並且旁及納尼亞傳奇的完整七部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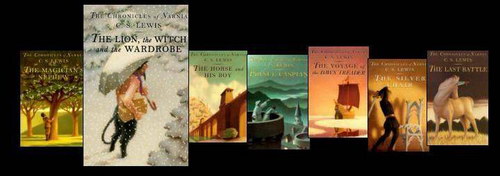 |
| 納尼亞七部童話全集 |
一、東西文化根本的人性處境差異:
要詳盡描述《獅王、女巫、魔衣櫥》的精神世界,就得先了解東西文化根本的人性處境差異。
東方文化的人性處境是『因緣論』的世界觀,發揮地最淋漓盡致的價值系統以正信佛教為代表。它認為,原本世界是無始無終的清淨合一最高境界,但是因為種種不知何故的原因(無明),產生種種因果相生相傳(十二因緣論),從而產生我們所處的大千世界。一個人處在這種世界觀,如果要追求終極的真善美,就必需回到最原始的無始無終最高境界(也就是涅槃)。回歸真善美的方法,就是積極去理解眾生的因果現象實貌,拋棄自我意識的偏執;從而阻止進一步的因果相生,才能回歸涅槃。於是,這樣的人性處境反映在藝術人文作品中,會積極呈現『凡事都有因果』、『看開、看透』、『回歸自然』....種種的『逍遙意境』,因而其美感經驗會發生在呈現逍遙美感的作品片斷與結局。
西方文化的人性處境是『始終論』的世界觀,發揮地最淋漓盡致的價值系統以基督教為代表。它認為,世界有一個開始,而且會有一個終結;既然一切時空都有終結,這就意謂著由始而終的經歷要進行一個意義判斷(也就是最後的審判)。於是了解始終變得不重要,由始而終的種種經歷才是生命真善美的重大追尋。一個人處在這種世界觀,如果要追求終極的真善美,就必需讓個人的生命歷程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如此的最後審判才會有意義。走向這種真善美的方法,就是積極去參與現實世界的種種生活事物,從而發揮個人的獨特性,才能彰顯個人獨特靈魂的精彩。於是,這樣的人性處境反映在藝文作品中,會積極呈現『凡事都需要體驗』、『堅持、非如此不可』、『走入現實社會』....種種的『拯救意境』,因而其美感經驗會發生在描述拯救過程的豐富故事。
例如《魔戒》,習於逍遙處境的我們,很容易遵循『因緣論』的世界觀去強加解釋『為什麼危險萬分的魔戒是由弱小無能的哈比人承擔?』,當然可以獲得蠻有道理的『因為哈比人弱小,所以持有魔戒為惡的能力也變小。』看法。但是這樣的因緣論世界觀,無法滿足我們心中期待的『魔戒』英雄;我們會期待看到佛羅多如何自我修行勝過魔戒,但無論電影或原著小說都明白表示佛羅多完全無法勝過魔戒;於是我們明顯無法深入理解這個角色的深刻意涵,因而普遍沒有人喜歡這個角色──喜歡咕嚕的人反而多很多。
(註:關於欣賞《魔戒》的拯救意境,請參考:『魔戒與舒伯特的 D.950 彌撒曲』。)
要強調的是,這種人性處境的價值判斷,往往與個人信仰內容或宗教教義不見得直接相關;也就是說,時常存在深受東方文化影響下的基督徒,表現出非常標準的逍遙意境之追尋;也容易看到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下的佛教徒(例如出家的西方人),表現出連東方基督徒都比不上的拯救意境;所以這種『逍遙意境』或『拯救意境』並不是什麼是非對錯的答案,只是描述一種人生態度具體存在的現象而己。這種逍遙意境與拯救意境的根本差異,往往決定了很多東西藝文作品欣賞角度的重大差別。
二、東方藝文作品的逍遙美感:電影《臥虎藏龍》
李安執導的電影《臥虎藏龍》是一個展現逍遙美感的絕佳代表,透過李慕白、余秀蓮與玉嬌龍三個角色表達電影中的逍遙意境。

透過李慕白這角色描述一個武林第一高手的一生:他原本想與師妹余秀蓮攜手退隱江湖,但是除師仇外,他發現罕見的良質美材玉嬌龍擁有正道武功卻沒有正道氣節,於是企圖以理以力折服玉嬌龍使之棄邪向正;如此一個武林宗師正直無私的救世行為,非但玉嬌龍不領情,還為了拯救玉嬌龍而死於毒針。這樣的故事明顯揭示著,走入現實世界發揚正道,終究只是一場空的,人都死了還有什麼正道禮義呢?
|
 余秀蓮代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好女人』:電影情節設定她的武功僅次於師兄李慕白,意謂著她是武林第二高手的崇高地位,何以只是當一個小小鏢局的老板而不是威震一方的掌門人?從故事可知,原來這是標準的『在家從父,父死從兄』;因為開鏢局的父親死了兄長也早夭,所以身為『好女人』當然不配擁有武林第二高手的自我實踐,只配繼承父兄的鏢局了。但是做為一個重視人際和諧的『好女人』,爭取自我實現而傷害人際和諧當然是不允許的。余秀蓮不但放棄自我的實現,連帶當她聽到年輕美貌的玉嬌龍必需奉父母之命嫁給老醜王爺,她也只能好言相勸『做好女人要認命,反正父母絕不會害你的....』。這就是電影中何以余秀蓮和玉嬌龍的打鬥配樂都如此充滿張力,因為兩人的人生觀實在差太多了! 余秀蓮代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好女人』:電影情節設定她的武功僅次於師兄李慕白,意謂著她是武林第二高手的崇高地位,何以只是當一個小小鏢局的老板而不是威震一方的掌門人?從故事可知,原來這是標準的『在家從父,父死從兄』;因為開鏢局的父親死了兄長也早夭,所以身為『好女人』當然不配擁有武林第二高手的自我實踐,只配繼承父兄的鏢局了。但是做為一個重視人際和諧的『好女人』,爭取自我實現而傷害人際和諧當然是不允許的。余秀蓮不但放棄自我的實現,連帶當她聽到年輕美貌的玉嬌龍必需奉父母之命嫁給老醜王爺,她也只能好言相勸『做好女人要認命,反正父母絕不會害你的....』。這就是電影中何以余秀蓮和玉嬌龍的打鬥配樂都如此充滿張力,因為兩人的人生觀實在差太多了!
這樣一個華夏社會人人稱道的好女人,李安也毫不留情給了一場空。如此重視人際關係,硬是對玉嬌龍下不了殺手,也無法放棄鏢局而與師兄雙宿雙飛;好女人的脾氣修養甚至當面對愛人死在懷中的悽慘處境,還得忍下憤怒情緒對玉嬌龍好言相勸,而不是一劍劈了她。這樣人人稱道的好女人有什麼下場呢?電影沒有明示我們也可以看到暗喻:如此好女人不是注定了只能縮在無用鏢局裡為無緣的師兄守寡?這種好女人仍然是太悽慘了,終究還是一場空。
|
 玉嬌龍代表理想自我的實現:處在社會禮法結構下,她唯一可以充分發揮自我的只有武功;於是『劍』成為一生追求的代表,不顧性命搶奪青暝劍正是追求理想熱情的燃燒。其實她是極為敬佩李慕白的,因為李慕白代表一生最高理想典範:成為武林第一高手。但是李幕白的『正道』與余秀蓮的『好女人』是分不開的,拜李慕白為師並遵守師命,幾乎注定就是得依照余秀蓮的禮教嫁給老醜王爺。做為一個追求理想的玉嬌龍當然絕不會接受,於是敬佩李慕白但不遵循李慕白與余秀蓮,遂轉變成搶劍與拒絕拜師。 玉嬌龍代表理想自我的實現:處在社會禮法結構下,她唯一可以充分發揮自我的只有武功;於是『劍』成為一生追求的代表,不顧性命搶奪青暝劍正是追求理想熱情的燃燒。其實她是極為敬佩李慕白的,因為李慕白代表一生最高理想典範:成為武林第一高手。但是李幕白的『正道』與余秀蓮的『好女人』是分不開的,拜李慕白為師並遵守師命,幾乎注定就是得依照余秀蓮的禮教嫁給老醜王爺。做為一個追求理想的玉嬌龍當然絕不會接受,於是敬佩李慕白但不遵循李慕白與余秀蓮,遂轉變成搶劍與拒絕拜師。
如此強烈追尋理想自我的人格,到最後竟然也是一場空。尊敬的理想典範李慕白竟被自己害死,追逐理想竟帶來理想幻滅,那人生也只是一場空了,所以跳下山崖成為最後的出路。
|
這三個人物,無論是人格崇高的第一高手、人際謙和的好女人還是理想熱情的自我形像,最後都只能造成一場空;這就清楚說明了李安這部電影要表達的是『逍遙處境』:現實世界不存在任何意義,只有『無』才是一切。所以這部電影的取景與鏡頭必定以表達逍遙美感為主,據此而論,李慕白與玉嬌龍的竹林之戰可說是逍遙美感的絕佳代表。
同理可看出,張藝謀的《英雄》、《十面埋伏》等作品,對比他先前的寫實批判風格電影如《大紅燈籠高高掛》,很明顯走向逍遙意境的表達。《英雄》的劇情固然有爭議且明顯斧鑿,但是表達逍遙意境的目標使我們不論劇情只論取景之下,明顯看出無名與殘劍的湖上比劍悼念飛雪是最美的鏡頭,導演用心之深遠勝談論六國統一的大道理。
這些逍遙意境的藝文作品反映的是我們對人性處境根深地固的價值觀,於是我們很容易沈醉在美感也很容易分享交流,就算簡單如日片《現在,很想見你》我們也可以輕易感受逍遙之美融合清純愛情的感動。
相對的,如果是拯救意境,我們就可能『受感動,但說不出為什麼』。
三、代表西方『拯救意境』的《獅王、女巫、魔衣櫥》:
 《獅王、女巫、魔衣櫥》與《魔戒》一樣都是老少閒宜的精彩故事,但是它們都是承載豐富精神意涵的偉大藝術作品。很多人都能認識其中的人性處境,只是說不出來,理由僅僅是因為我們很少有機會進行『拯救意境』的多元價值省思,這是很可惜的。 《獅王、女巫、魔衣櫥》與《魔戒》一樣都是老少閒宜的精彩故事,但是它們都是承載豐富精神意涵的偉大藝術作品。很多人都能認識其中的人性處境,只是說不出來,理由僅僅是因為我們很少有機會進行『拯救意境』的多元價值省思,這是很可惜的。
始終論的人性處境重視真實生活的體驗,讓人生不斷尋求一次又一的經歷與冒險。這些經歷與冒險的結果不見得都是喜劇收場,《魔戒》中的老洛汗王希優頓就是最好的典範。這個角色在電影中的改編有點難以掌握原著中的面貌,所以我透過原著描述他。希優頓曾經老朽過,但是並不像電影中那麼誇張地直接被壞巫師薩魯曼佔據身心;從原著來說,是因為他己經戎馬半生終於讓國家獲得和平後,就失去冒險經歷的雄心,導致寧可相信佞臣巧言,才會腐化到六親不認。當升級成白巫師的甘道夫去見希優頓時,不過是把巧言制服罷了,再來他只有告訴希優頓『重新拿你的劍,就可以獲得力量!』;這個意思就是說,希優頓之前的腐化,就只是缺乏人生投注熱情燃燒的目標而己。
重生的希優頓有沒有得到生活的平安?沒有,他選擇一條重新燃燒生命的道路,直接導致他戰死沙場。就因緣論而言這真是不懂趨吉避禍的執迷不悟,或者是為了照亮別人自我犧牲的道德聖人。但是就始終論而言卻是『砍倒敵方黑蛇大將而志得意滿,在生命最光輝的一刻猝死。』,也就是說,他經歷了一生最精彩的生命歷程,完成他的使命,讓生命之始與生命之終記上獨特的經驗,這是遠比自己是否道德聖潔或趨吉避禍更高的人生意義。所以在《魔戒》原著中充滿了哀傷與犧牲,托爾金不會誇示『站在善良一面邊就可以永保平安』這種媚俗的喜劇,很容易導致因緣論世界觀的讀者難以分享這種重視生命歷程的藝術感動;雖然人人都受感動而喜歡欣賞,但往往說不出來為什麼感動。
《獅王、女巫、魔衣櫥》同樣是表現人性處境的『拯救意境』之電影,一開始,露西走進衣櫥,便出現明顯的『始終論』人性處境。

就始終論的世界觀而言,每個人的意義在於他多彩多姿的經歷,這必定產生『偏好冒險』(偏好改革)的人格特質。相對的,因緣論既然以消除因果為要務,能減少是非的『偏好保守』人格特質自然被高舉。露西第一次走進納尼亞,明明衣櫥出口仍大開,她卻大膽地走進森林中;遇到人羊雖然嚇了一大跳,但隨及主動進行接觸寒喧;後來知道人羊被捉走了,立刻想到的是不顧一切冒險找方法救人。這種『偏好冒險』的人性觀與我們社會習慣的自掃門前雪式『偏好保守』實在相差甚大,甚至到了隱藏身份安全無虞的網路社會仍然如此,可見基本人性觀有多大的差異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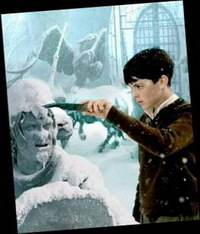
愛德蒙一開始雖以反派登場,但原著或電影皆詳細描述他走進白女巫皇座的過程,那絕不像是被下迷藥的呆子能做出來的。他得克服忘了穿大衣的刺骨寒冷、克服看到巨大石像的恐懼感,甚至看到血口大開的惡狼也不會嚇昏。這說明白女巫的土耳其糖不是單純的迷藥:它更適切的寓意是,給愛德蒙錯誤的努力目標,讓他經歷人生時走向錯誤目標。所以用歌德《浮士德》中一句:『人在努力時,總不免有迷誤。』來看待更是恰當。
|

彼得成為王中之王的歷程更是明顯:他本來只是一個青少年,但是承受聖誕老人的寶劍盾牌後,他必需超越自己的能力去成為王中之王。這種自我超越如果發生在東方藝文作品,一定描寫成彼得努力進行自我能力提升的修行;但是無論原著或電影都掌握了始終論的特性:彼得成為王中之王的經歷,不是靠自己努力的修行,而是莫名奇妙地跌了一跤來殺死惡狼。換句話說,他不是擁有成為王中之王的才能而被獅王選中,而是他被獅王選中後才培養出成為王中之王的經歷。同樣的,他與女巫的大決戰也無法靠自己得勝,只能奮力盡責,仰賴選中他的主宰給予冥冥之中的幫助。這跟《魔戒》中佛羅多不是因為有能力抵抗魔戒才被選中,而是被選中後才經驗魔戒重擔是一樣的人性處境取向。
|
這種始終論的特性,相信有一個主宰決定了世界之始的目的與世界之終的審判,並相信人類總是在被選中的處境中不斷冒險經歷成長,那他們必定相信存在一個主宰能主動幫助經驗人生的每一個人;否則,一個人任意冒險,會是多危險的事!如何保證露西亂闖納尼亞不會被害?如何保證愛德蒙的迷誤不會永遠沈淪?如何保證彼得不至死於惡狼之口?這就是獅王亞斯蘭的重要喻意。
四、凡自強不息者,終將能得到拯救:
其實若我們真的成為冒險者,如同愛德蒙般走向偏差的機會大得多了,這正是歌德在《浮士德》前半部的感嘆:『人在努力時,總不免有迷誤。』;但是,到了浮士德的結局,歌德卻體會到『凡自強不息者,終將能得到拯救。』。這種信心與盼望,正是獅王亞斯蘭的第一個重要喻意。
王中之王彼得被賦與的使命是『領袖』,於是他得冒險經歷各種他能力做不到的領袖事業,包括決鬥、戰略等種種邁向王者的經歷。電影的改編與原著有一大差異:原著中彼得並不知道亞斯蘭死了,他只是如魔戒中的亞拉岡一樣儘力打一場必敗之仗,因為那是必需經歷的一個使命過程;於是,他成長為『偉大』的彼得王。如果你看過完整的七本納尼亞傳奇,就會在續集電影《賈思潘王子》(Prince Caspian)的故事中繼續看到彼得的使命歷程。換句話說,毫無成為王中之王能耐的彼得,只有存在並且相信一個超越性的大能者亞斯蘭,他才能歷經危難不至失敗;這是『凡自強不息者,終將能得到拯救。』的第一種型態。
曾經陷入迷誤的愛德蒙,正因為曾經體驗過最深層的善惡拉鋸,從而體會非凡的判斷力,這也是為何善惡大戰時唯有他知道先砍魔杖的策略。所以他變成『公正』的愛德蒙王,在《馬與小孩》(The Horse and His Boy)這本續集中有清楚謀略與是非堅持。這是很有趣的,若是在東方社會,能成為公正之人必定是從小修行成果非凡的好人;但是在始終論的世界觀,卻轉變成只有親身體驗善惡拉鋸的人才能真正公正。也就是說,人在奮鬥時,不但有彼得那種能力不足的禍患,也可能有愛德蒙這種來自人性缺陷本質的迷誤;只有存在亞斯蘭這種人生的陪伴者,方能保證人生冒險時不致因為一時的迷誤導致永遠的沈淪;這是『凡自強不息者,終將能得到拯救。』的第二種型態。

露西是獅王最疼愛的『小孩子的樣式』,而這種『小孩子的樣式』是信任亞斯蘭之下的冒險個性;所以在本故事中她是最早發現納尼亞良善面的小孩,在《賈思潘王子》是獅王亞斯蘭最信任的傳信使,在《黎明號的遠航》(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甚至為了『看不見的人類』冒險闖進巫術環繞的暗屋。這是最幸福的一種人,她只要勇敢面對生活就會有單純的快樂與平安,所以她才會是『勇敢』的露西女王。
|

相對的蘇珊卻是代表『現實』的人性,她不但長得最漂亮也是最討世人喜愛的小公主、眾人追求的女王(這是原著的設定,當然你未必同意電影中的演員也如此),所以她不但避免冒險、避免戰爭(《馬與小孩》)甚至常常把現實放在神蹟之上(《賈思潘王子》)。現實的人生也可以是非常單純的,所以在本故事中蘇珊與露西一樣受到獅王的疼愛,並且成為代表『現實』之『溫柔美麗』的蘇珊女王。但是在《最後之戰》(The Last Battle)中,蘇珊卻選擇再也不回到納尼亞了;所以她代表的是『凡自強不息者,終將能得到拯救。』之反面,如果放棄自強不息,往往就得不到生命最高的意義了。
|
這就是歌德領悟的『凡自強不息者,終將能得到拯救。』,這種始終論的世界觀並不是看重人生奮鬥的結果,而是看重奮鬥的過程。人生太容易欲善成惡也太容易欲惡成善,企圖靠自我修行來解決難關更是難以達成;是故,以成敗論英雄是完全無意義的,只有忠於展現獨特自我地經歷自強不息的生命冒險,才能得到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在這種處處陷阱的人生冒險中,亞斯蘭成為信心與盼望的力量。
五、超越因果循環的愛與救贖:
了解這種始終論的世界觀後,就可以體驗白女巫的『古老秘密』與亞斯蘭的『更古老秘密』了,這是路易斯寫作本書的中心喻意。
 因果循環是一個非常清楚且合理的法則,犯罪的要受處罰,背叛的要承受後果;愛德蒙自己選擇了與白女巫同路的惡因,當然就得接受『凡與白女巫為伍皆死於絕望』的惡果。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古老的秘密,這只是非常合理的因果循環;獅王代表自由快樂的生活,與他同路當然獲得喜樂;白女巫代表絕望的力量(納尼亞第一集《魔術家的外甥》己經表明,偷吃蘋果得永生的女巫必然是充滿絕望的生命),與之為伍自然只有絕望與死亡。這種因果循環當然不能被打破,打破了這世界上就沒有正義與公理了。 因果循環是一個非常清楚且合理的法則,犯罪的要受處罰,背叛的要承受後果;愛德蒙自己選擇了與白女巫同路的惡因,當然就得接受『凡與白女巫為伍皆死於絕望』的惡果。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古老的秘密,這只是非常合理的因果循環;獅王代表自由快樂的生活,與他同路當然獲得喜樂;白女巫代表絕望的力量(納尼亞第一集《魔術家的外甥》己經表明,偷吃蘋果得永生的女巫必然是充滿絕望的生命),與之為伍自然只有絕望與死亡。這種因果循環當然不能被打破,打破了這世界上就沒有正義與公理了。
所以只有違反因果的愛與救贖才能打破因果循環的法律,電影的對話或翻譯似乎沒有掌握到這個重點,在原著中,『更古老的秘密』是:『如果一個完全無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死了,那麼石桌就會裂開,那人就不會真死。』。而電影的中文譯句卻是『如果沒有背叛的人代替背叛的人死了』(大意如此),這實在差太多了。
從因果循環的立場,任何一個沒有背叛亞斯蘭的人代替愛德蒙死了,仍然通通落在因果循環內。如果露西代替愛德蒙死了,那是兄妹之情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是水獺夫婦替愛德蒙死了,那也是人之常情,因為他們深信只有四兄妹同時健在才能拯救痛苦的納尼亞;如果是其他會講話的動物替愛德蒙死了,那會莫名奇妙甚至可能是被脅迫誘騙的,無緣無故為何替別人死?只怕白女巫也不答應。所以無論是誰替死,通通落在因果循環內。
 亞斯蘭的替死則完全不同:他本身完全無罪(這當然是故事的設定),他甚至創造了『與白女巫同行者必死』的法律審判,所以他代替愛德蒙死是唯一徹底違反因果循環的事件;因而能打破因果定律,讓象徵『與白女巫共同犯罪者必定死』的石桌裂成兩半;於是,被殺死就得下陰間的因果定律也不復存在,他才能違反生死定律地重新復活。 亞斯蘭的替死則完全不同:他本身完全無罪(這當然是故事的設定),他甚至創造了『與白女巫同行者必死』的法律審判,所以他代替愛德蒙死是唯一徹底違反因果循環的事件;因而能打破因果定律,讓象徵『與白女巫共同犯罪者必定死』的石桌裂成兩半;於是,被殺死就得下陰間的因果定律也不復存在,他才能違反生死定律地重新復活。
世界上怎麼可能有如此不合常理地打破因果循環?這就是始終論世界觀的信仰與盼望了。因為勇於冒險的人,他將會越來越發現靠自己的實在太少,莫名奇妙得到的幫助實在又太多;如果因果定律牢不可破,勇於冒險的人早就該徹徹底底失敗而死光了!因此,顯然存在著超越因果循環的力量,讓習於冒險的人性可以安然存活,這就是亞斯蘭代表的『愛與救贖』之力量。
很明顯的,這種愛世人、愛世間、愛彼此的愛是不同於親情、友情與愛情的另一種愛;它發揮了一種救贖的力量,讓一時迷誤的愛德蒙得以脫離因果循環的危險;同樣的,保護了彼得、蘇珊與露西的納尼亞冒險過程。也由於這樣的信仰與盼望,讓勇於冒險經歷生命的人們不會懼怕種種失敗與危機;因為他們知道存在一種愛與救贖的力量,可以保護每一個人自強不息地尋求。
六、回歸人性深層的心靈渴求:
其實納尼亞的故事只是很簡單的童話,連帶著改編後的電影也更加適合輕鬆賞玩,何以需要這麼長篇大論地分析內在精神呢?
 對於路易斯來說,納尼亞的故事實在太簡單了,四個小孩子敢如此冒險是理所當然的,他只要努力描述獅王代表的愛與救贖就夠了。然而,對西方兒童如此簡單的觀念,在我們東方社會卻未必能詳細理解;因為牽涉到的是立足點徹底不同的『因緣論』與『始終論』之巨大差異,我們理應習慣《臥虎藏龍》式的逍遙美感,《魔戒》或《納尼亞傳奇》式的拯救意境如何能讓我們喜歡?結果很明顯的,《魔戒》受到瘋狂喜歡,《納尼亞傳奇》至少也受到熱愛童話故事的大人與孩子瘋狂喜歡;這就可以猜想是否是一個人性深層的心靈渴求之問題了。 對於路易斯來說,納尼亞的故事實在太簡單了,四個小孩子敢如此冒險是理所當然的,他只要努力描述獅王代表的愛與救贖就夠了。然而,對西方兒童如此簡單的觀念,在我們東方社會卻未必能詳細理解;因為牽涉到的是立足點徹底不同的『因緣論』與『始終論』之巨大差異,我們理應習慣《臥虎藏龍》式的逍遙美感,《魔戒》或《納尼亞傳奇》式的拯救意境如何能讓我們喜歡?結果很明顯的,《魔戒》受到瘋狂喜歡,《納尼亞傳奇》至少也受到熱愛童話故事的大人與孩子瘋狂喜歡;這就可以猜想是否是一個人性深層的心靈渴求之問題了。
除了極少數例外,每一個人都需要具有價值感的心靈生活;逍遙意境的心靈渴求與拯救意境的心靈渴求應該是平衡的,可惜社會往往會偏於一方。如果過份走向逍遙意境,會導致個人與社會趨向偽善與虛無;過份走向拯救意境,會導致社會與個人趨向恐怖主義的狂熱。在台灣以網路社會而論,PTT的歷次鄉民事件可說是過份走向拯救意境的罕見事端;除此之外絕大部份的現實社會與網路社會,我們往往受到無形的價值觀不平衡之壓迫:我們發現,這個社會徹底的高舉逍遙意境而鄙視任何拯救意境。於是,流傳不絕的網路謠言徹底走向虛偽的騙局,告訴我們千萬不要在車禍現場救人不然會被反咬肇事(真的有這麼白痴的法官嗎?)、告訴我們每一個職業人都是存心騙錢所以越便宜越好(完全不需要尊重個人的專業?)、告訴我們所有進行社會運動政治改革的人通通都是別有私心的假仙(所以完全不要關心社會事務?)........
於是,我們徹底揚棄任何一點一絲冒險式的體驗生活,甚至在網路社會這種虛擬的安全環境也怯弱地放任詐欺與鬧場者之惡行;然後,被壓制過度的拯救心靈通通轉化成瘋狂的政治意識型態發洩出來。
對這種鮮明的拯救意境式電影有感動,會不會是另一種發洩內心拯救心靈需要的管道?無論如何,納尼亞雖然只是童話,但是對於真誠面對自己內在拯救意境心靈的大人們,卻也是釋放自己心靈渴求的一大契機。如果你對《魔戒》與《納尼亞》有莫名的感動,或許,正因為它走進了你心中被壓抑的拯救意境。那你不妨試試閱讀納尼亞全集,再加上路易斯的成熟之作《裸顏》;也不妨進階閱讀到貝多芬的後期弦樂四重奏,或歌德的《浮士德》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那麼,你可能發現一個全新的心靈世界。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