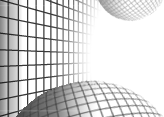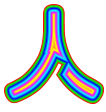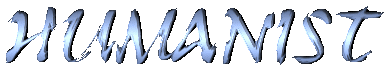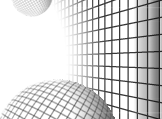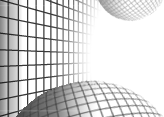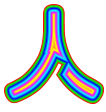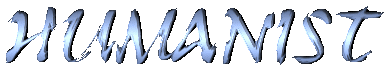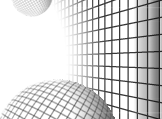|
說起女性主義與同性戀平權運動這兩個熱門話題,我們當然可以由社會運動史的角度分析其來龍去脈,並就其聲援弱勢的角度,來談談這兩類社運對台灣社會造成的衝擊...。但因著篇幅所限,也因著我個人對女性主義與同性戀平權議題所引用的理論基礎有些隱憂,因此決定跟讀者們談談這兩個運動的理論基礎,以及基督教信仰對這些理論基礎的回應。
女性主義,同性戀議題與後結構觀點
同性戀議題在世界各地都不是單獨存在的議題,它與女性主義議題,幾乎可以說是有孿生姊妹或兄弟的關係,因為其背後的理論基礎是極其類似的。在台灣一樣是如此。
任何一個運動若要推展開來,造成兼具廣度與深度的影響,就必須在運動與經驗之外,同時建構其理論基礎。女性主義與同性戀議題所源引的理論基礎,都是「後結構」理論與「心理分析」理論。
我們先來看看「後結構」理論。
遠在理性主義時代,人類曾深切相信世間有某種恆定不變的觀念存在,人透過語言符號去捕捉這恆定不變的觀念。正是因為這信念,科學發展在理性時代一經啟蒙,就滾雪球的越來越興盛。
但出現一位馬克斯,發表震撼世界的理論「人的理性很大幅度上是受意識型態影響的」,弗洛伊德發表近似觀點「人有根本不為自己所覺查的潛意識,所以理性不可靠」,人類的思想史就開始重新反省「人類的理性」這曾如此篤定確信不疑的課題。延續並改良馬克斯理論,並融合弗洛伊德心理學的修正,便出現了「後結構主義」。後結構正是反理性浪潮下的高潮產物。其代表人物德希達與傅科,蔚成自文藝復興理性主義時代以來,最大的反理性主義反人道主義的力量。
後結構理論完全推翻理性主義的觀點,認為人類根本沒有所謂的恆定不變的觀念,一切都是意識型態的產物,而人類用語言將這意識型態固定下來,因此要不斷的質疑語言所傳遞的觀念,從質疑中再重新去界定出新的觀念。德希達將這必須不斷的質疑語言符號在社會中的意義的過程,稱之為「意義的耽延」,意義是永遠無法被確定下來的。
至於傅科,則從其知識考古學(Archaeology)和系譜學(Genealogy)研究中,暴露「思維主體」「中心結構」「本質主旨」等理論的遊戲成分,所有的知識(觀念)都是生於特定的權力系統,用特定權力的語言表述出來。這權力系統包含政府,教育單位甚至是家庭組織等等。
後結構因此質疑理性時代以來高抬的理性地位與人道主義地位,所有想當然爾的觀念,不過是歷史與政治所產生出來的語言,是需要重新被質疑被界定的。理性與人道,在特定政治與歷史的擺佈下,根本就成為了不合理結構的「共謀」。
後結構觀點,女性主義與同性戀平權運動如何拿來作自己的理論基礎呢?很簡單,眾多需重新被定義的「語言」,從女性主義來看,就是「女性」的定義,從爭取同性戀平權者的角度來看,就是「自然的男性本質」與「自然的女性本質」的定義。
女性主義認為過去對女性定義──溫柔的,持家的,陪襯男性的,非理性的──等等的界定,需被質疑。同性戀平權者則認為「男性本質」「女性本質」也無所謂的生物學自然學的基礎,一樣是一種特定歷史與政治下的語言,是可以重新被界定的。生下來生殖系統的外在是男性,並不表示就是本質的男性,他一樣可以是女性的性自我認同。
從這裡,我們就發現女性主義與同性戀議題,為何也源用心理學,特別是弗洛伊德到拉岡的心理學範疇的原因了。
女性主義,同性戀議題與心理學
女性主義者對弗洛伊德是又愛又恨。恨的原因是弗洛伊德的最有名的理論之一「陽具中心論」,很明顯的把女性視為一種「匱乏」,顯然有貶抑女性的共謀。但弗洛伊德對嬰孩前期的性不穩定論──嬰孩並無性別身份,非女亦非男,是一個多元變態體,同時具有發展陰性或陽性,異性愛同性愛的潛質──卻也成為女性主義者與同性戀平權議題很喜歡源引的理論。既然嬰兒前期無性別身份,當然就沒有所謂的性別上的自然本質,女性男性就不必然非得要呈現出某種模式才叫做「自然的」。
而常被列為後結構主義的心理學界代表拉岡,更因其與弗洛伊德領域相類的「鏡像研究」,將性別主體指向並非與生俱來,而是語言,欲望,潛意識互動的結果,因而被女性主義者與同性戀平權者引用。語言,欲望,潛意識都是由歷史建構的,所以拉康進一步把性別主體非穩定化,揭櫫主體內部的多元分裂與矛盾,全盤推翻理性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傳統心理學中所預設的和諧統一立體觀。
從上面兩種領域──後結構與心理學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女性主義與同性戀之所以經常相繼出現並存於弱勢團體運動中,是有他源引理論上的相似性的原因的。然而,女性主義還是和同性戀議題有某種微妙的張力存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女性主義者在爭取女性平權時,不管如何重新定義女性,至少需要確定自己的女性性認同身份,但就因此經常被同性戀平權者斥為「生物學的自然本質主義」,就同性戀者看來,尤其是可以與異性也可以與同性做愛的雙性戀看來,根本就毋需界定所謂的女性與男性,人之出生乃無性,或雙性的,沒有所謂的「生物性的自然本質」,何必在乎自己是女性還是男性,反正全都是語言的歷史的政治的產物。
引用後結構與心理學的困境
所以很矛盾的,女性主義用後結構理論解構掉男性主體文化的同時,同性戀平權者也用後結構理論解構掉女性主義者必要的堅持,而雙性戀,一樣的又用後結構觀點解構掉某些同性戀者只與同性性愛的堅持。
九零年代在台灣產生出來的弱勢團體邊緣戰鬥,從大原則來說,是與基督教信仰中對社會正義的堅持絕不相違背的。正因為商業與資本主義對政治甚至是文化事業的收編,才需要透過無孔不入的後現代時代的傳媒,並透過非政治管道的運作──即邊緣戰鬥的形式──來為弱勢團體爭取權益。
但同時,因女性主義及同性戀者所源引的理論,卻對基督教信仰造成衝擊,使基督教信仰不得不審慎的面對這兩類運動。
首先就是後結構理論。
後結構提醒人面對各類觀念時不宜太過想當然爾,也不要對人類的理性太過篤定,他提醒基督徒應常常反省自己「言說上帝」「言說正義與愛」時的時代處境,不要以有限的語言去固著那比語言本身更豐富的事物。
但是,後結構既是處理「時代」「歷史」,就不可能同時處理比「時代」「歷史」更無限大的事物,諸如「永恆」「上帝」,以及上帝在永恆中安排的「救贖」。後結構處理歷史與時代時,其自身一樣被歷史與時代所受限,也就是說,透過後結構所顛覆所建立的,日後也將被後結構方法所顛覆拆毀。我們光是看女性主義與同性戀平權議題同用後結構,卻彼此間有張力,多少可看出其建構本身的不穩定性。這就是基督徒面對後結構觀念時必須審慎的原因。
譬如說,女性主義者或同性戀平權者企圖推翻聖經,所依據的理由是「聖經就是權力運作下的書寫」,是「時代歷史的產物」,一定會造成跟基督徒徹底的決裂。今天不管處理文學批判的人,是如何的發覺某聖經經卷絕非古老相傳下來的作者與年代,都無法據此推翻「聖經是上帝透過聖靈,讓人書寫出救恩」的信仰。既然聖經牽涉到「上帝」「聖靈」與「超越時間歷史時代的救贖」,它就已經遠遠超越人理性所能理解,是需要用信心去回應的範疇,也因此,它就不是後結構方法可以硬性處理的範圍。
此外,如果一個人根據後結構理論宣稱聖經的「霸權書寫」,他的前設就一定必須是「聖經只是一本書」──當然,這前設一樣必須是一種「信仰」:信仰絕對沒有上帝;或者信仰有上帝,但是這上帝不跟人說話;或者信仰上帝說話,但是絕不透過書寫說話....。既然一樣有信仰前設,當然跟基督徒的對話就是「有前設的信仰」與「有前設的信仰」的對話──這意思就是說,要求基督徒把聖經視為「只是一本霸權書寫」,這要求本身就是在用自己的信仰前設,強迫別人放棄自己的信仰前設,這顯然很不合後結構主義企圖建立的「對話精神」。
至於女性主義與同性戀平權者對心理學的引用,就連心理學界不同派別間,都無法沒有微詞。譬如兩者一再提倡性別乃「非生物性」「非本質自然」的,是由社會建構出來的「社會建構論」立場,心理學界自身就無法達成共識。因為心理學界一直就有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與社會建構論(constructionism)兩種觀點的爭論。更何況對心理學的引用本身就很易導致非常多元的解釋,無法定於一尊。舉例而言,當弗洛伊德宣稱小女孩因發覺自己沒有陽具而產生「閹割恐懼」,導致女性本身就是一種匱乏的男性主體理論時,就有女性主義心理學家反諷的研究出小男生因發現自己沒有乳房與陰唇而產生恐懼意識,因而男性是一種匱乏的女性主體理論。這種兩極化研究,徒然讓人懷疑心理學這條路線的研究太易導致多種論說,容讓太多前設,解釋太多元了。
重新定義屬這時代的伊甸園男女
其實基督教信仰與女性主義不盡然是衝突的。許多女性主義者會拿基督教開刀,說它是迫害女性的幫兇,原因就是若干保羅言論中對女性的貶抑。針對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提出來辯駁的,就是文化比較必須以「水平時間」而非「垂直時間」的方式。在保羅時代,女性受歧視是全世界的現象,當保羅說「丈夫是頭」,其論點是「要像基督,以『捨己的愛』愛妻子」,這已是當時代非常大的突破。
而在基督教信仰核心中,絕並非沒有男女平等的觀點。這從耶穌與眾人相處並不刻意區別男女,尤其深愛馬利亞可知。最初男女受造,夏娃「幫助」亞當,這幫助原文含意也是指稱平等關係的幫扶,絕無夏娃低下伺候亞當的含意。男女不平等,是人類犯罪受咒詛後,帶出來的墮落文化──「女人要戀慕男人,男人要轄管女人」──這絕不是上帝創造的本質,而是一種墮落。
面對女性平權,基督徒根本不需質疑聖經,反而應當理直氣壯的回應後結構主義「重新定義」的挑戰,重新思考在這時代當中被救贖之恩挽回來的男與女,應如何回到屬於這時代的、被上帝喜悅的、伊甸園中的男女關係上。
至於同性戀爭取平權,是以宣稱「聖經中同性戀有罪的倫理觀已過時」為主要訴求,要基督教接受就比較棘手了。因為聖經的確有個信仰前設──每一次提到同性戀之罪,都並題信仰上的混亂,這混亂絕不只是不信上帝這麼簡單,還包括供奉其他神,必然伴隨的廟妓禮儀──包含有男妓女妓的性混亂。罪進入世界的結果,是使一切神與人間,人與人間,男與女間的關係混亂毀壞。而男女性別錯置,跟信仰混亂有絕對的因果關係──這前設是個信仰議題,牽涉到基督教對罪的嚴格定義,若宣稱只是時代產物,一種霸權書寫,就等於強迫基督徒不再把聖經視為其信仰核心,強迫基督徒毀壞信仰中對「罪」的嚴格定義,或更明確的說,是要基督徒放棄信仰中某種最重要的內涵,這當然是基督徒辦不到的。
此外,對同性戀平權主義竭力宣稱的「性是社會的建構,並不具有生物的本質的自然的性」,基督教信仰也很難認同,主要原因還是身為人類最初的亞當夏娃的受造,的確是一男一女,而非「無性之人」。基督徒無法不承認自己對性的看法在某個角度上正是一種「本質的自然的」性生物學。
同性戀是時代中人應當共同承負的苦難
當同性戀者提出自己的被環境影響的,或不明原因影響的,所導致的同性戀頃向,是一種需要被同情被理解的弱勢,基督教基於上述原因,儘管仍視之為罪,卻應走向令一種角度的關懷與理解──對於這樣無從改變的同性性趣,應將其視為這時代的共同「苦難」。
同性戀之所以變做一種苦難,乃是因為它是人類的墮落罪惡下的一個犧牲品,就像女兒被人性扭曲的父親亂倫,或商業物化下貧苦人的賣淫,只讓當事者自身承負痛苦罪責,顯然不合理,但不能據此宣稱與父親發生性關係,或貧苦者賣淫是合理的。
因此這時代中所有人都應做到不去誤解醜化同性戀者,憐憫其苦難,伸出接納安慰的手。儘管如此,仍不能不視其為「病」與「罪」,也不能去美化它,因為苦難不應被人拿來當淒美的藝術品,而應被人共同承負並努力去消解掉──否則終有一天,文化墯落後的一切混亂,包括亂倫雜交,都可以用同樣的後結構方法,以後世文化顛覆先前文化,最後變成完全沒有倫理的基礎。
基督徒永遠無法避免在倫理議題上傾向保守小心,理由不僅在於社會性的制衡,更在於信仰前設──神創造世界的確曾有個伊甸園,但被這世界遺忘了。因此不管是生理本質的,是社會建構的,是理性人道的,是反理性反人道以求達到更人道的...,都只能在人類歷史中不斷證明──人類終其歷史,距離完美是何其之遙遠。
(本文出自宇宙光雜誌1996年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