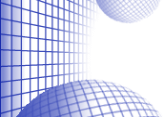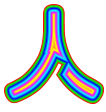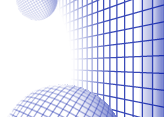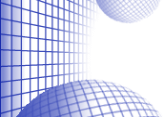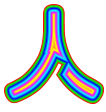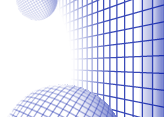這份讀書報告將簡單的整理此學期方法學讀書心得,主要以再現(Representation),擬像 (Simulacrum)為主,輔以其他參考資料, 以詹明信及布希亞的後現代理論為主要梗概,再由目前正在展出的台北雙年展、上海雙年展及C02台灣前衛文件展,將所學的理論與當代作品嘗試對話與解析。
首先來細看Representation與Simulacrum文中,兩位作者都是由柏拉圖的再現說(或應說是模仿說)娓娓道來「再現」一詞在歷史上的源由,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que裡,對於模仿有相當嚴厲的批判,他的理型論讓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一個相對應的「理型」(idea),以床為例,第一層次是床的理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事物的本質,是所謂處於黑暗洞穴中無法契及的永恆之光,第二個層次是現實上體現理型之實用的床,由理型主導工匠製造出來的實物,第三個層次才是畫家模擬第二層次之實物所畫的床,這已經遠遠背離事物的本質「理型」,是模擬再模擬,是錯誤的宣稱。在這心靈抽象概念高於一切知覺呈現的國度中,繪畫家處於被譴責為次等模仿者的劣勢,此時的藝術不能傳達真理訊息,甚至可能敗壞人心,縱容慾望和情緒。另外在Sophist文中,柏拉圖以埃及藝術與希臘藝術之間的區分,將影像的製造分成二階級,一是以埃及藝術為例之「製造與生命形體相似之物」:making of likeness (eikons) ,二是如希臘藝術「製造與外觀相似之物」:making of semblance (phantasms) ,前者是再現空間三維的比例上模仿,像是複製一樣(copy),為了呈現永恆宗教性的理念而作;相對上較劣等的後者是希臘雕塑家及畫家製造的作品,常常為了觀者的立足點更動空間比例,他們是為了看起來美(appear beautiful)去做,不是依真實的空間比例。在柏拉圖一方面推崇永恆性的理念,一方面貶抑表象美感的同時,擬像(simulacrum),也就是虛幻不實的幻影(phantasm),在藝術史上就一直處於位階更高的真理之陰影下了。
到亞理斯多德的時代,主觀及物質感官開始介入,視覺感官產生符號之指示性作用相對於闡示想像力及記憶的幻影(phantasia),但是視覺(sight)仍離不該心靈的統攝,它不過是「最接近」心智(mind-like)的感官系統。簡單的敘述了影像如何在歷史上居於劣勢,接下來看看關於representation 的字源,追溯回拉丁文,repraesentatio,是一種連接在動詞”to be”的句法結構,praesens 則是praeesse的分詞,也就是”to be before”之意,這可有兩種解讀,其一是單純空間上的、前置性的介係詞;其二是含有更高層次意義的優先權、或是領導、支配力,在這樣的概念裏,不是遙不可及的過去或未來,而是正在手中的當下,「現時」的重要性就被突顯出來。而擬像(simulacrum)的字源,拉丁文中的simulacrum 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為幻影(phantasm)或 外表、外觀(semblance)。相較之下,「再現」似乎是佔有了時間的諭意,而「擬像」是空間上的關係,這在擬像的討論部分會有更進一步的說明,於布希亞的論述中,擬像甚至成為行動之中的,有自主能力的存在。
略去由先後高低層次導引出的中古時期representation 的垂直性面向,直接進入Francis Bacon及Descartes的現代經驗主義及啟蒙時代,此時不需再像柏拉圖害怕影像削弱人的心志,或是混淆現實甚至取代現實,反之是隨著對自然的了解,駁斥宗教上的圖像學,以及Bacon 尋求事物的合理性,藉著實證經驗來探索現實世界進而重塑人類的新世界,加上尼采及笛卡兒的理論,「我」或是「主體」的參與,再現及影像製造的問題就變成「如何產生」,而不是「像不像」或是「像什麼」的問題了。相對於中古世紀的垂直面向,笛卡兒強調心靈與感官視覺在平行面向的不平衡性,強調是由心靈「看」到的符號(signs)而不必須用眼睛直接與視覺有所關聯,再現就不再以視覺形式為主,不必以像不像為基礎,只剩下由內因性生成的錯覺來作為代表。由此似乎可以很快的連結到尼采、佛洛伊?、甚至德悉達的後結構主義, 不過還是不能不提Simulacrum一文作者還談到的意識形態形成的過程中,再現之地位的轉移,不是兩極化的本質性或純感官,而是處於溝通的位置,不再重視優越與否層級位階的純理論,而是實作上的「為什麼」(why)與「如何」(how)。在這相當「現代性」的觀點中,我將進入下一部份擬像及後現代的討論。
那麼,到底什麼是後現代呢?德法系統的後現代先驅者例如傅科、布希亞、羅蘭巴特、德勒茲、德悉達等人似乎都不曾明確為自己冠上這標籤,看似相論戰的李歐塔與哈伯馬斯(有學者認為兩者毫無關係)把現代與後現代之爭搬上了檯面,詹明信也許是少數願意正面去面對後現代這怪物且說法比較中肯的一位學者,雖說他的理論應稱為晚期資本主義比較恰當。首先,讓我們視野轉移離開歐美主流文化,看看這些術語的使用來源:在後現代性的起源(註一)一書當中,考證了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現代主義(modernisim)兩者都誕生在很遙遠的邊緣地帶,來自於拉丁美洲的西語國家;1890年達里歐(Ruben Dario)從法國的浪漫主義派、象徵主義派之中,取用現代主義(modernismo)這個字彙,並且針對西班牙的統治提出了 「文化的獨立宣言」;而後現代主義亦是首度於1930年代在西語世界登場,狄歐尼斯(Federico de Onis)最早開始使用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o),他利用這個詞彙描述在現代主義自身中一種保守的反射,一股渴望強大的、熱情奔放的挑戰,不久他又提出這只是一個短暫的存在,接著會出現一個「極端現代主義」(ultramodernismo),使得激進的現代主義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此書的作者將起源與城市串聯起來,一路從利馬-馬德里-倫敦-上海-吳哥-猶加坦-紐約、、、巴黎-法蘭克福-慕尼黑,從文學、政治、經濟、詮釋到社會文化,相當精采。不過在此我只想點出其中有趣之處,從起源來看不難發現,不管是現代性也好,後現代性也好,不管論述者想不想被其標籤,兩者或多或少都與邊緣性格、反抗或反對主流的態度有關,不論是相對於主流文化之延續或斷裂,兩者基本精神之中的質疑、批判、否定性都很相像。如同沈清松先生所談到(註二),「現代」與「後現代」是應該連貫起來思考,後現代並不是現代的結束,它事實上是現代的延續甚至是加深;在「現代」的精神裡面就包含某種二元論的思考,它希望透過「現代」來針對「傳統」,用「新」來針對「舊」,如同文藝復興之後以人為中心而不再以神或宗教為核心;所謂「後現代」也是同樣精神的延續, 因著無法接受「現代」的種種困境和弊端,希望藉著否定及批判找出新的面貌。簡單從沈先生的文章整理出「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之間的關係,現代性的特徵有三:
- 第一是「主體」的哲學,以人作為認知、價值、權力的主體。
- 第二是「表象」的思想(註三),透過表象的組織,代表或是表達這個社會,這又可以延伸到科學、藝術、政治各個方面。
- 第三是「理性化」的歷程,透過有規則的方式來控制活動的進行,且因著科學、藝術和規範三個活動本身的專業化和自律化,有不同的表現。
相對的「後現代」的特徵就是對「現代性」這三點之反動:
第一,批判由主體哲學延伸而來的主體過度膨脹,以及其中權力與所謂追求有意義之生活衍生出來的問題。
第二,質疑「現代性」之中的表象之追求以及何謂「真實」的問題。
第三,對於現代中「理性」的成分之懷疑,當然也一併否定過度工具化的理性。
簡單了解了現代與後現代的關係之後,接下來的重點將以討論布希亞關於擬像的著述,闡明表象與真實的問題,然後再以詹明信的著述為主,對於其所謂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再討論。為什麼選了這兩位呢?主要原因是詹明信的書算是各大師之中較容易懂,較為中肯的全面性論述,對於日常生活及社會文化轉變的全面性檢討,有著正面的啟發和意義;而布希亞先知預言式的傳道,及其催眠惑眾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吻,是相當有趣的部分,更何況虛擬世界似乎在過了上一個世紀末還依然是纏繞不休著我們,今年的台北雙年展就以「世界劇場」為名,不偏不倚的呼應了德波(Debord)之大作「奇觀的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93)。提出這二者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因,總覺得法國人好像老是丟了炸彈就跑的感覺,反省是很深入闢裏,但除了深刻的思想啟發之外,相較之下美系的思想看似平面、淺顯,卻有樂觀的實際行動力。不論如何,各式各樣的理論本應互補相輔相成吧。
在提及布希亞之前,不能不談一下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相對於布希亞較為悲觀的洞見,麥克魯漢又可說是比較正面且抱持著樂觀希望。二十世紀影像製造頗具重要性的媒材首先是攝影,它助使擬像成為雖複雜卻有效的指涉,也促進搖動現代主義王國的基礎。攝影的複數性及可再複製性不但挑戰原本具有 「獨特氣息」、「氛圍」的藝術品,也質疑了藝術界相關的權威、客觀、原創、獨一等人文立場的假設,如同Walter Benjamin 的著作中,對於「靈光」消逝的感嘆以及傳統精緻文化之衰敗,伴隨工業社會帶來的新的價值觀與傳統價值的衝突。但是這慌亂與喧鬧似乎不曾停息,接下來的科技發展更將我們帶入了數位網路的時代,在這個世界裡,正如麥克魯漢的宣言一般:「媒介就是訊息」(Medium is the Messsage) (註四)。在他樂觀的論述中,無孔不入的媒介(或譯:媒體)本身比其所傳遞的內容或訊息都更重要,身置於這媒介的過程其實可以帶給我們一個全新的「地球村」,這科技浪漫主義使人類可以回到未有文字之前的社會,回到印刷物出現之前那類似於「部落」的,完整而和諧的情感;藉由資訊科技的力量,可以超越具體世界而邁向統一。藝術家在其中的角色扮演著「探針及觸角」的作用,持續不斷送出理論以檢驗媒介,形成覺醒和預警的系統,稍後將提到的C02台灣前衛文件展,就形成這樣的一個介面平台。麥克魯漢將媒介視為感官的一種延伸,他的樂觀似乎仍維繫在以人為中心的理性,其營造的虛擬世界也就迥異於布希亞對於擬像所發揮的極致--「虛擬就是真實」(註五)(The simulacrum is true) 。
在1967年Gilles Deleuze發表的論文The Simulacrum and Ancient Philosophy,作者試圖「反轉伯拉圖思想」,使擬像在重要的評論及藝術史中更能附合我們的時代,此理論取代了柏拉圖式的模範(model)優先於複製(copy)的先後順序,宣稱擬像(simulacrum)不需要複製(copy)。使擬像的地位提昇且確定在圖像(icons)及複製(copies) 之中的權利,問題不再是區分本質與表象、或是典型與複製,而應該完全消除這些區分。不去區分,但差異仍然存在。到了布西亞的擬像,此差異也不再被需要了,因為,「再也沒有模仿的問題,甚至於是拙劣的模仿也沒有。問題只在於取代真實本身的真實的符號,…幻覺不再是問題因為真實也不再是問題」(註六)。 布西亞擬像之理論,前所未有的深深影響了藝術批評,雖然在很多的後現代論述當中好像忽略了這位大師,他所提及與舉出的例子的確反應了相當多的現實狀況。像美國的迪斯耐樂園,被其指稱為「糾纏複雜之秩序的擬似物之完美模型」,整個國家就是一個擬像,像是可沉溺於溫暖、靈巧舒適的嬰兒期一般的後現代奇異空間。他完全顛覆了所有西方理念的維繫:「符號可以指出深處的意義、符號可以與意義互相交換取代-----當然這個取代的意義已被上帝所保證。但是如果上帝本身也可被虛擬,也就是說,其降低至構成信仰的符號? 那麼整個系統就無足輕重了。除了巨大的虛擬物再也沒有其他東西存在;不是非真實,而只有虛擬物,在一個失去了參考與既定範圍,永遠無法停止的循環中,不再是與真實之間的交換,而是自己與自己交換」 (註七)。
布希亞此預言式的宣告伴隨著人們對於工業社會和科技發展的焦慮與懷舊復古的情緒之最高點來到,不僅僅是在視覺的領域,生活中的新科技完全轉變了傳統溝通的方式。大眾媒體對於藝術的衝擊模糊了所有藝術博物館及其空間與大型購物中心之間的界線,像是同時刺激也同時回應了編年史(註八)中媒體對於削弱真實的策略。其中指出電視及錄影帶影像從一開始就提供了虛擬的功能,什麼是現實中存在或感覺得到的真實不再重要,人們花絕大多數的空閒時間盯著家裡小小的銀幕,與其中無數閃過眼前的再現的紀錄,漸漸模糊了真實與舞台上的界線,模糊了什麼是真正發生的,什麼只是在網膜上被刺激的。更有趣的是,他進一步區分異化(dissimulate)與虛擬(simulate)的不同,「異化是假裝沒有擁有自己其實已經擁有的東西,相反的虛擬則是編造(feign)自己擁有事實上並不擁有之物」(註九) 。
他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在一個裝病的病人身上,很有可能裝得太逼真而有了「真實」的病症,這也就是精神官能症一直處於醫療中曖昧不明之因,如果一種病是能被「製造」出來的,那麼針對治療「真實」疾病的醫藥就在此失去意義,後現代性當中所強調之自我與他我界線(ego-boundary)的消失,和所謂精神分裂式的情境就產生了。是故不難想像,擬像不再是靜態的存在,而是一個接著一個不停的擴延,成為永無止境令人追逐不斷的形象。而形象(image)與擬像的關係可由其對於形象的四個階段來分析:
- 第一, 形象(image)是基本事實(profound reality)的反應(reflection);
- 第二, 形象遮蔽(masks)且曲解(denature)了基本事實;
- 第三, 形象遮蔽了事實的不在場(absence);
- 第四, 形象與事實毫無關係,自己有自己的次序,擬像的邏輯。(註十)
於是,事實不必在場,擬像就這樣與大眾媒體、科技生活、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共舞,一步步的侵蝕進而取代所有傳統中再現的真實與信念。我們一直以來所相信的真實與虛幻之別,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感,回憶、記憶、期許以及關於理想和希望,都將解離漂浮散失在這擬像的虛無之中。
本書Simulacrumu 一文的作者指出,布希亞惡夢般的藝術觀並沒有為影像文化提供任何建設,許多對於這位法國理論家的批評在於他忽略了新大眾媒體影像帶來的正向效果與提供另類觀點及學習各種差異,不僅是單一種「大哥」的理想主義而已。《知識的騙局》(註十一)一書的作者更用「胡言亂語的聲調」來形容布希亞混用科學術語及非科學語彙以譁眾取寵,指出若是去除所有這些花言巧語,他的思想將剩無一物。而在藝術實作方面,當布希亞提到擬像控制了我們每天生活的時候,他忽略掉近十多年來許多藝術家已不斷的尋求剖析、批評大眾媒體,也諷刺地將其放置在許多作品之中。以這樣的提醒作為引言,我們再來看看詹明信的說法。
同樣是探討二次大戰後急速變化和發展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由馬克斯主義提供靈感的政治分析之後現代主義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集中焦點在敘述另一個異於布希亞的模式,依循擬物性的另一軌跡,提到德波(Guy Debord) 於1967發表的著作《奇觀的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指出由於傳播媒體將個人世界發生的事件一一轉變為受宰制的媒體奇觀與演出,世界的歷史已被轉變為 「虛假的事件」及 「壯麗的場景」。詹主張,擬像的文化適當而足夠的進入了我們生活,在其中所有的交換價值已經被普遍化,使得每一個價值的記憶都終將消去。(註十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可以用他舉出以電影為例,在其中過去的一切被呈現為懷舊(nostalgia)的參考,並不是歷史內容實際的再現,而是藉著意像的處理來傳達時尚風格的屬性(註十三);我們身旁周遭的環境亦是如此,像是近來很流行的社群標示所謂「五年級生」、「六年級生」,讓大家很快的找到認同點;標明著校園民歌金韻獎的CD可能被放在綠標的櫃子上,但是再包裝之後的「五年級的回憶」的CD也許就能晉身入排行榜了;回憶的真實價值不再是重點,在這個充滿符號的消費世界,不過是要滿足懷舊的情緒,懷念對象本來的面目很可能完全無關緊要。
細看詹明信的理論,不能不先提及什麼是「晚期資本主義」,以便更了解他所論述的大環境:基本上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具有某種立場傾向的官僚控制網;第二,政府和大企業是息息相關的。還有跨國的企業形式、國際勞力重新分配、新形式的媒體關係、電腦和自動化的全面滲透等等,都是此時期的特色。在藝術史的方面,他以生產模式為劃分標準,將資本主義與藝術形式分成三個階段(註十四):
- 一是市場資本主義對應於寫實主義;
- 二是壟斷式帝國主義對應於現代主義;
- 三是跨國資本主義對應於後現代主義,也就是論述的重點。
他認為現代與後現代並不是一個連續的關係,因為兩者所處之經濟系統是完全不同的狀況,更具「馬克思」意味的想法是,「後現代是一種力量場域,各種文化的推進力必須在此奮鬥前進」(註十五),應使用一種支配性的文化邏輯或準則的概念來評估異與同的差別。由他對於後現代構成特點的分析可以更了解其想法(註十六) :
-
第一, 後現代具有一種新的無深度性,在當代理論及擬像文化裏找到其延伸。此無深度性是相較於過去的數種深度模式,例如:本質與表象的辯論模式、佛洛伊德的壓抑及外顯的模式、真實與非真實的存在模式、還有語言學中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之間的模式,這些都是後現代所對立的,取而代之的是慣例、論述、和文本遊戲,在此也透露出後現代文化中的平面性、多元性、破碎性及非結構性;
- 第二, 具有一種隨之而來的歷史性的削弱,不只是在於大眾歷史中,個人的時間性也形成新的形式和語法,如拉岡的精神分裂結構(schizophrenic),包括主體的分裂及去中心化;
- 第三, 具有一種全新的感情基調,作者將之描述為「強烈性」(intensities),可以回到古典的「崇高」(the sublime)理論來了解。主體的消失伴隨個人情感的消逝,取代的是非個人性的、自由飄動的欣快感(euphoria);
- 第四, 具有一種與嶄新科技之間的深刻的構成關係。此時期的科技不再像是過去渦輪的機械動力,也不是冒著煙的工廠和煙囪,取代的是電腦與電視,再也沒有任何表徵性的力量,生產的象徵,只有不斷複製的過程。作者所提出的後現代建築之疏離性讓我聯想到網路般複雜的高架道路應是一個最好的典範,它改變了城市原有的相對空間,個人的身體再也不能與既定環境有恆定性的互動,持續相對變化的結果讓個體的心智和身體迷失在各種溝通的網路中,就像開車上高速公路時依賴的不是生理上的方向而是各種標示符號的指引,出口也不在於心之所向,而是預先布滿又常改變不定的匝道。
以上這四點涵蓋了文化、歷史、感情、科技生活四個面向,可以更實際也更廣闊的運用在思考及分析今日龐雜的亂象。相對於布希亞所發揮致極的擬像的「破壞性」,詹明信的理論多了許多浪漫的理想色彩及使命感,也多了些樂觀的行動力,不用著眼於布希亞悲觀的虛無,而能正視實際面臨的社會文化問題。
Simulacrum一文的作者Camille在論及後現代論述之後,提出了史學家憂心的反思:那麼一個人該如何寫下一部「擬像的歷史」,而不是「藝術的歷史」? 基於影像不是再製或取代真實,卻是遇到了完全處於另一秩序的真實--或者是所謂布希亞的超真實(hyperreal)--那我們迎面而來的就會是一部不能宣稱是關於物體,而是關於虛擬策略的藝術史了。這般擬像的歷史將會與我們傳統所學教科書上的故事相差非常多,重新用這擬像的角度來看之時,在再現的歷史上將會缺少那些偉大躍進的時刻,也就是那些基於技術上對於模仿的偉大進展的部分。取代征服真實(模仿)的是,一個虛擬的藝術歷史其將會是逃離真實--或應說是不再有我們所認知的真實--而處在想像和幻覺之王國的故事,有著慾望同時也包含了無限恐懼的故事,讓事物從依賴眼睛和文字中解放的故事。如此一來,歷史還是不是由一連串的「偉大作品」所建構而成就是一個更大的難題了;相反地,一個適當的虛擬歷史勢必可對於任何一件宣稱具有個別權威性的藝術工作提供再議的可能性,後現代所強調的主體破碎、個體消失及物化、深度的失去、時空的斷裂、結構的去中心化等等,都反映了當今所處的環境之中,相對於現代性所產生的質疑和批判。如此看似海市蜃樓一般、卻又「真真實實」無所不在的虛擬世界,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自處?
嘗試著簡單整理兩位學者的論述之後,再回來現實生活中藝術領域裡能看到些什麼;遠古以來人類追問不斷的本質與再現真的無法希求、不復存在了嗎?虛擬的真實就一定帶領著世界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天外飛來一筆的奇想:關於後現代這擬像的觀點,說穿了會不會不過還是一種復古(沒有了歷史感的懷古),回到柏拉圖時期尋求理想中的本質性,相對上反藝術的狀態?靈光消逝的現今突顯的是更為本能式的感官世界及外在形式﹖
 |
| 陳界仁的《凌遲考》 |
 |
| 侯聰慧的《戀戀風塵》 |
 |
| 蜜芮安 (Miriam Backstrom) |
 |
| 蒙塔達斯(Muntadas) |
今年的台北雙年展以「世界劇場」(Great Theatre of the World)為題,這名稱取自於十七世紀西班牙知名劇作家科爾德隆(Pedro Calderon, 1600-1665)的同名宗教戲劇,原本的內容是以戲中戲的手法敘述人類的命運。此次策展人有意將美術館當成一個劇場舞台,展覽的作品則為演出的腳本,觀眾則成了參與演出互動的角色。展覽的平面廣告與特刊的封面是一巨大的紅色遮幕,垂落下來在小小的縫隙之間透露出舞台後些許燈光,這樣的設計成功吸引我們目光焦點,甚至是急欲窺看究竟的遐想。遮幕從十七世紀以來為了在換景時遮蔽觀眾的視線,分散注意力,讓幕升起時劇場和舞台想要營造出來的幻象視覺效果更為逼真,造成了幕前幕後兩個世界,幕昇幕落之時空裏,真實與虛擬的區別。場景從古典劇場慢慢轉換到現今當下之時,遮幕本身似乎不再擁有那麼孑然二分的作用,整個時空已經是一個奇觀的世界,劇場或是藝術不再是模擬真實的本質,不再於幕起時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我們本身就是敘事者,遮幕已然成為我們的演出道具之一,每一個人都是整個虛擬時空之中的演員,無時無刻不時彼此傳遞著演出的訊息和影像。回首觀看今年的台北雙年展,在這樣的奇觀世界裡,想說些什麼呢?策展人王嘉驥先生的文章中,不難發現此次展覽的中心思想是相當內斂反省式的,不再製造更多喧囂的藝壇奇觀,而是希望找到一種重新凝視的觀賞模式,能夠超越環繞在我們週遭早已奇觀化的花花世界,再次尋找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以期許重新檢驗和審視人生。作品如陳界仁的《凌遲考》影片(正如詹明信在《空間》一文中所提到的「暴力展示」”atrocity exhibit”和重新安置於後現代空間的疏離寫作與紀錄)(註十七) ,侯聰慧如同另一場演出的後台紀實,捕捉《戀戀風塵》拍攝現場的「失焦」照片,蜜芮安 (Miriam Backstrom)一幕幕無人跡卻如假包換的生活場景,蒙塔達斯(Muntadas)類似古代圓形劇場的三面螢幕,播放天災、戰爭、暴力事件的紀錄及兩側鼓掌不斷的觀眾影像,,,都表達了對於權力結構的質疑,時空轉變的無奈,都會及現代工業社會的孤寂感,以及控訴媒體傳播的暴力等等。策展者目標寬宏且遠大,但也許是因為此展覽的內省及沉澱思考的成分居多,其實在走入展場之後的疏離感頗強烈,總覺得這樣的方式能夠帶給群眾什麼樣的思考和互動呢?如果自身不在這藝術史或是社會劇場的脈絡演變之中,能夠清楚的了解自己是在幕前、幕後,或甚至是抽離在整個體系之外?
 |
 |
| 康居易的《危機四伏》 |
 |
 |
| 嘉義鐵道藝術村《援助交際51天》 |
 |
 |
| 汪承恩的《狗道理》 |
 |
| 陳宏明的《原慾交響曲》 |
台北雙年展或許是超越幕前幕後的思考反省,那麼C02台灣前衛文件展或可視為幕後充滿活力的生動排練。相對於雙年展的嚴肅凝視,C02文件展的多元和包容性讓觀者輕鬆的掀起簾幕走入展演空間 (展場的單元設計是以一個個自屋頂垂落的C型白色塑膠幕簾),一起融入生活化的舞台。如同Simulacrum一文中所寫到的當代藝術特性:無處不在的裝置藝術相對於繪畫、環境藝術相對於雕像、表演藝術相對於圖示在過去十年來藝術家的生產當中都背離外在的再現而轉向感覺經驗的王國,可以使用德勒茲另一個重要的語?來說,虛擬不是真實的錯覺而是確立整個感官的王國。在此次文件展中可親身體驗,溝通的系統不是基於真實不真實的觀念,而是基於視覺相對位置參數本身,也就有關是誰在看,從那裏看,而不是他們在看什麼,是真的還是想像的問題。像是:康居易921大地震之現代社會寫照的《危機四伏》,嘉義鐵道藝術村的《援助交際51天》,汪承恩以諷刺挖苦表現的矛盾時代《狗道理》,陳宏明揭發情慾與權力糾結不清的《原慾交響曲》等等;
雖說C02文件展裏許多創作作品不難發現隱約之中前人已經表現過,甚至雙年展裡也有的痕跡,但是就如同展覽發起人一致的共識,這將開創一個不預設觀點也不採用事先議題,迎接多重與歧異,希望能中肯而完整的呈現台灣當代藝術之面貌,搭建一個可以交流且激發藝壇活力,不斷延續的新平台。這樣的開放性相對於官方雙年展也許是個獨特的生機,雖然沒有深刻嚴肅的思考提醒 (好比歐陸的哲學性),或者多了些零散、破碎,也不能說它將能引領我們走向何處,但相信在每一次幕起幕落之際,在這個失去焦點的世界裡,期待成為每一個就在身邊的新希望的開始。
最後再將場景切換至上海雙年展,在這個奇特的城市裡,人們與世界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呢?如果用之前兩位學者的論述相較來看,絕對是遠離布希亞游牧飄移式的虛擬母體,實實在在的踏入詹明信可觸可及的積極建設面,更像是古典劇場在嚴密的排練周延之後正正式式揭幕演出。展覽以「都市營造」為主題,探討都市文化與建築的問題,對應了短短十年來上海巨大的變遷,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趨勢,這城市本身就是一個豐富的劇場;不同於台北雙年展向內凝視的內省與反思,也異於C02文件展的年輕活力,相對的是藉由建築這「凝固的歷史」之展現,多了許多更高更遠更兼容並蓄的世界觀。如同策展人阿黑娜斯提到的,這個展覽探索了都市環境中的建築,和當代藝術的互動,揭示了一種更寬廣的建築定義,與藝術之間愈加模糊的界線。這也一並將視線延伸到「為藝術而藝術」的限制性,超越實用主義,功利的想法,進入現實生活環境的美感經驗。遊走在新古典主義的展場空間裡,順著第一個迎面而來徐冰的裝置作品《鳥飛了》,帶領我們的想像力像飛鳥一樣展翅鳥瞰,在文化視野上進入沒有疆界的國度,作品如安吉拉•布洛克(Angela Bulloch)的《宏觀世界》伴著BBC新聞片頭曲的粉彩電視牆、陳幼堅的《京都,我的愛人》將不銹剛材質裝置成充滿禪意竹影婆娑,還有皮埃爾•于格(Pierre Huyghe)的錄
像裝置《莊嚴的合唱》,像是虛構的城市建築之間摩斯密碼般的溝通方式。上海雙年展雖沒有開腸剖肚的批判性,沒有過度堆疊的理論,縱使脫離不了傳統的制式觀點,努力迎向國際文化交流的嘗試是非常可貴而值得學習的。
| 安吉拉•布洛克(Angela Bulloch)的《宏觀世界》 |
| 皮埃爾•于格(Pierre Huyghe)的錄像裝置《莊嚴的合唱》 |
對我而言,過去一直未曾仔細的接觸當代理論和當代藝術,這個學期的方法學開展了一頁全新的視野和思考,其實在翻閱當代著述同時也感受到比古典傳統思想更為切身而與生活息息相關。很淺顯的整理一些書摘式的理論,加上正好有機會參與並加以比較兩岸三個同時演出的當代展覽,希望也是一個讀書整理以及全新的出發點。這篇期末報告的命名應是幕前幕後或是幕後幕前,是先有本質在前,蓄勢待發的表演在後;或是永遠衍生不斷的擬像在前,而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的實體在後,就讓我學學本書中許多作者喜歡用的弔詭的結束語,,,這就留待當道的語言結構學家來進一步闡示吧。
註解:
- The Orugins of Postmodernity by Peery Anderson 1998. 王晶譯, 聯經出版社1999. 這本書的來源本來是為了介紹詹明信的新書《文化的轉向》(The Cultural Turn)
- 《從現代到後現代》沈清松,哲學雜誌第四期1993年四月pp4-25
- 這裡我個人認為若改成「再現」的思想,也許更好。
- Marshall Ma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1964.
-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1981,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heila Faria Glaser 1994. p1
- Ibid. p19
- Ibid. p5
- Jean Baurillard.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1986
- 同7. p3
- 同7. p3
-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Fashionable Nonsense 蔡珮君譯, 時報出版2001
-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1991, p18
- Ibid. p19
- Ibid. pp35-36
- Ibid. p6
- Ibid. pp6-45
- Ibid. p156
參考資料:
- The Orugins of Postmodernity by Peery Anderson 1998. 王晶譯, 聯經出版社1999.
- Marshall Ma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 1964.
- Christopher Horrocks. Marshall Mcluhan and virtuality 麥克魯漢與虛擬世界
楊久穎譯 貓頭鷹出版2001
-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1981,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heila Faria Glaser 1994.
-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Fashionable Nonsense 知識的騙局, 蔡珮君譯, 時報出版2001
-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1991. Duck university press.
- Fredric Jameson, 後現代主義, 吳美真譯, 時報出版,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