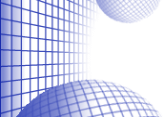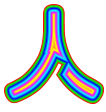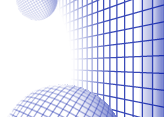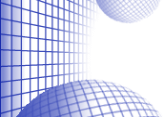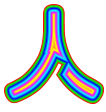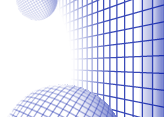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
【Oliver Sacks著,孫秀惠譯(1996):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台北:天下文化】
每個領域裡都存在一些勇於突破傳統框架、力圖從當代的領導典範中抽身
而出,轉而反身性地檢視那些在同行中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方法論與問題意
識,並進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或者回復過去曾有、現已被遺忘的——詮釋
角度以抗衡/補充當代典範視域所力不能及的天才型人物:
19世紀末的哲學家尼采以極富個性魅力及思想穿透力的批判文學筆觸,重
現了希臘神話原典裡的悲劇精神,糾舉出西方自蘇格拉底以降的理性主義傳統
之欠缺感性、直觀、狂醉等詩人性格的「生命意志」(will to power) 力量的不完
整性,震撼了20世紀的西方哲學、神學及藝術文化界。
20世紀的盧力亞(A. R. Luria)與薩克斯(O. Sacks)兩位醫生,則力抗神
經學界的主流:「定位論」(localism)對於人類心智功能所採取的化約式機械論
觀點,要求重回肇始自紀元前「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延及19
世紀前半葉的那條帶有濃厚人文色彩的醫學敘事傳統,將現代醫院中一本本由
醫學專業術語及去個人主體性的病史描述所堆砌成的病例資料,還原回一連串
具生命力的動人敘事,再現了19世紀末那場神經學典範論爭中處於較邊緣的一
方——「整體論」(wholism)所強調的、對於人體生理官能及主觀生存體驗進行
統合性關照的人文精神。
盧力亞與薩克斯寫過的幾本介於醫學與文學之間的作品,如《記憶大師的
心靈》(盧力亞)、《睡人》及《火星上的人類學家》(薩克斯),以神經醫
學臨床病人的生命敘事為主軸,刻畫他們如何因腦神經的機能異常而相應發展
出一套各具特色的心智功能調適機制及其間的生活歷程,均在當代英美文化界
成為震撼一時的暢銷書。
此種結合神經學病理資料與心理學敘事角度的創意書寫方式,已逐漸改變
一般人對於醫師「只問病症不問病人」的刻板印象;而此類「神經紀實文學」
的科普功能,不僅漸使非專業的讀者得以從其豐富的臨床案例敘事中獲取與實
存生活經驗相關的神經學常識,同時也能讓讀者與作者一同看見這些不同的故
事主角如何在面對各自心智功能障礙的挑戰時,仍能展現他們各自動態多元的
自然生命力,大大開放了主流刻板印象中「只有心智功能正常的人才是完整的
人」的狹隘人類學觀點。
從敘事的角度——也就是一個以第三人稱為主要人物主詞的敘述角度——
看人,將一切用以衡量他/她在某種後天的能力分類架構上的測驗結果或診斷
名詞均擱置一邊,使其重新回到我們第一手感受意識下的現象學目光前,作為
一個擁有其尊嚴與獨特生命形式的自主心靈,「敘事取向」不僅在當今由機械
論主導下的神經科學界是邊緣的,即便是在強調「尊重個別差異」的特殊教育
實踐中也是一個從未佔據問題意識中心的冷僻觀念。
在行為心理學的制約下,主流特殊教育界所尊重的「個別差異」,僅僅指
涉那些個別學生在教育治療意義下的不同特質及需求。師生關係的方向是徹底
的「由『我』看『你』」:由那位知識水準與價值品味均高於「你」的「我」
替你規劃理想的生活範式,教育你、改變你;而非讓學生成為能夠享有自決尊
嚴、保持自主距離的他者,任其以無限的可能寬度摸索出獨特的生命方向—─
「我」的角色,只有在能幫助「您」實現您的自我願望時,被動地提及。
「我們的測驗和方向,我們評估的方式是嚴重的不足。它們只顯出我們的缺陷,卻顯不出我們的能力;當我們需要去了解人在音樂、語言與戲劇的能力,觀察一個人在自然狀態下,顯現自然的能力時,它們卻搬出方塊拼圖和一些系統條列式的問題。」
(Sacks著/孫秀惠譯,1996:298)
1970年代美國特教界喊出的「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口號,乍看之
下似乎頗吻合於去標籤化的人道主義理想,但「誰是主流?」、「主流與非主
流何以不能並存?」等問題,更如錘鍊般地迫人省思一向高舉教育愛的身心障
礙教育之後設人類學視野寬度——是否在最深層的意義上,它仍舊是作為教育
家所擁有的一種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呢?
為何只因為大多數人天生心智功能正常,我們便能判定:凡心智功能不如
此運作者「必定」無法擁有在屬他/她標準下的正常生活?前工業革命的農業
時代,又需要怎樣的特殊教育?20世紀的台灣,特教老師教智能障礙學生「實
用」的語文、「實用」的生活技能,一整套教育訓練計畫的目的竟是寄望他們
能更適當地嵌入這個本就不以他們為主要預設使用者的社會制度,豈不是一種
自相矛盾嗎?
《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書中提到一個名叫娜蒂雅(Nadia)的女孩。她
是一個擁有繪畫天賦的自閉症者,經過相關的「治療」後,在開始學會說話的
同時卻停止了繪畫。按照治療人員所預定的教學目標,只要這位自閉症兒童能
開始與人進行社會性的互動,這個結果可以被視為是「成功的」案例。然而回
到敘事角度的觀照下,「她」則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囚犯——被剝奪了享受
天賦才能的樂趣,被囚於一個口語環伺的世界;在那裡沒有欣賞的眼神歡迎著
她私下獨處時的繪畫創作,卻偶而存在著願意在大庭廣眾下包容她正起始而不
甚暢達之語言能力的善意。
「成為一個孤島,與世隔絕,就一定雖生猶死嗎?那可能是一種死亡
,但卻不必然如此。雖然失去了與其他人、與社會、文化的『水平』
關係,他們仍然擁有重要而密切的『垂直』關係,就是與自然、與
真實之間直接的關係,這樣的關係不受外在影響、干預,別人也碰
觸不到。」(Sacks著/孫秀惠譯,1996:374)
——獻給對開放心靈的熱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