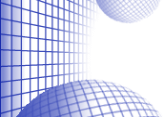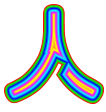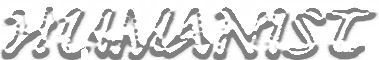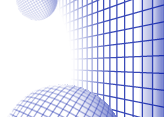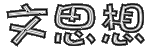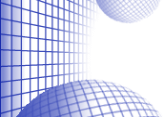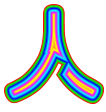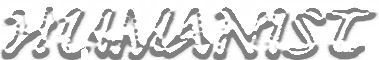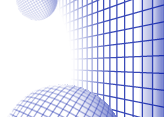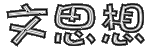「涵攝、歷程和境界開顯−唐力權場有哲學述評」
作者:宋繼杰(吉林大學哲學系)
出處:哲學雜誌第13期(July
1995)
唐力權場有哲學的三大貢獻:
1.
以「場有」超越「實體」觀念
2.
比較哲學
3.
生命哲學
壹、場有哲學本質
一、「場有」概念的形成及其含義
1.「場(Field)」的意義:
(1)「場」的概念最早是由科學家法拉第提出,他把磁力在空間中的分佈變化狀況稱為磁場,帶電粒子周圍電力線的分佈變化狀況稱為電場。因此「場」的初期概念包括連續性的空間、力量和方向三要素,後來物理學的發展,「場」不僅包含空間,也可以包含時間甚至更多維度的空間。一般自然科學常見的「場」還有「流場」、「應力場」、「重力場」、「量子場」等。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將重力場視為時空的扭曲,換句話說時空並不是獨立的,而是會受到所有具重量物質的影響;另一方面,「重力場」固然是因物質而生,卻可以不依存於創造它們的物質而自存。
(2)除了物理學外,心理學中的格式塔(完形)理論也是建立在「場」的概念上。
(3)「場有」的「場」,是指「事物的相對相關性和為此相對相關性所依據的根源所在」。換句話說,「場」就是事物所存在的一個複雜、動態的關係網。
2.「場有」概念的形成:周易與懷德海−對西方傳統哲學的批判
(1)簡單位置:牛頓的物質觀念,在時間、空間中一定佔有一個固定的位置(坐標),而與其他位置無關;休謨進一步將「印象」具體化,賦予類似物質的簡單位置觀念。懷德海批判這種固定、瞬間的簡單位置觀念,並不是人們的自然經驗,而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把抽象當作具體,是一種「具體性誤置的謬誤」。
(2)實體概念:亞里斯多德首先提出了「實體」的概念,笛卡兒進一步發展為物質實體和精神實體。物質實體在空間中有簡單位置,精神實體在時間中有簡單位置(休謨稱為「印象」)。懷德海批判這種實體概念,並不存在現實經驗中。現實經驗的終極要素是「事件」,實體不過是一連串事件的抽象組合。後期懷德海以「現實存有」取代實體作為宇宙的終極要素,它是以「存在的最完全意義」而存在的事物,既是現實的,又是潛在的;既是因,又是果;既是主,又是客;既是生滅,又是永恆;既是實在,又是現象;既是全體,又是部分;既是過去,又是現在;既是時間的,又是超時間的。
(3)懷德海以「現實存有」為終極要素,這是「場」的本體論,是一種「機體哲學」,又是「創造哲學」,有機創生作用與「現實存有」的「超切」(既超越又內在)關係構成了宇宙的真實圖像。這與「周易」的「有機自然主義」或「有機過程論」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二者都是「場有」概念的根源。
3.「場有」概念的含義
(1)「場有」就是「場中之有,依場而有,即場即有」,一切事物都是屬於場中之有,是依存於「場」而有,而場本身也是有,有則是本於場。事物的「存有本性」乃在於其與「場」(週遭環境)的相對相關性,此相對相關性不僅決定了事物的「存有本性」,基本上它就是「存有本性」。
(2)「實體主義」把事物設想為完全孤立自存的東西,導致事物的自我封閉和僵化,「場有」的概念則相反,是開放而動態的。對於人來說,所面臨的不再是一個可以將其與自己對立、分離的實在,而是圍繞和支配他的事物之間的一種直接關係。人不是一個「絕對旁觀者」,而是置身於將其包圍、限制或他所關心、牽掛的「場有」的「場有者」。
二、「場有哲學」體系的基本框架
場有「是一個互相涵攝的真實,一個虛機了斷的真實,一個境界開顯的真實」,「互相涵攝是場有的實質/超切義,虛機了斷是場有的造化/歷程義,境界開顯是場有的處境/開顯義」,此三者構成場有哲學的蘊徼三義:「蘊構格局」、「造化流行」和「境界開顯」,亦即場有哲學可區分為三個內在關聯的部分−「關係論」、「歷程論」、「意義論」。
1.「關係論」:
(1)
從「關係」角度考察事物是「場有哲學」之異於「實體哲學」的最本質所在。事物既相關相對,就必有一個互相涵攝的「超切」關係。所謂「互相涵攝」就是互為限制、互為條件的意思。
(2)
基本的涵攝關係有結構與勢用(功能)、內延與外延(空間的相關相對)、前延與後延(時間的相關相對),及理數(抽象原則)、事數(具體表現)、象數(混成關係)間的涵攝等。
(3)
「場有哲學」的形上學,即是把世界看作處於永恆相對相關的活動之網中,是一強調聯繫的「關係學」。存有的本質在於「關係」,而「關係」是受整個宇宙大網影響而不斷變動的,因此沒有絕對的「物自身」或「實體」,這與「周易」的「生生不息之流」和懷德海的「過程哲學」的精義相近,而與「實體主義」迥然有別。
2.「歷程論」:
(1)
希臘哲學中,赫拉克里特斯認為萬物都是流動變化的,世上無不變之物,承認「變」而否認「不變」;帕梅尼德斯則相反,認為「不變」是常態,世上無真正變化,變化是感官幻象,是「非存在」。此後哲學家試圖調和二者在存有本性中,但「在萬變中求不變」仍是西方傳統形上學的終極關切。
(2)
懷德海以摒棄「在萬變中求不變」的思維方式為其哲學的根本任務,主張「歷程」乃是「現實存有」的存在本性。
(3)
「場有哲學」主張「場有」與「歷程」相互預設,「場有」的存在是由它的「歷程」或「生成」構成的。生成的歷程之於「場有」不是被動的發生或改變,而是「場有」包含「活動作用」於自身,「場有」自身就是「活動作用」。此種使事物產生變化,造成差別的「活動作用」,唐力權稱為「權能」,而「權能」即「場有」,「權能」是場有的權能,「場有」是權能的場有。
(4)
「場有哲學」以生成歷程為存有本性,認為每一個「現實存有」都是不同於其他「現實存有」的生成歷程,連續性是由一系列接續的生成單位所構成,這與赫拉克里特斯的「流變觀」不同,其差異如下:
|
存有本質 |
歷程觀 |
流變觀 |
|
連續性 |
連續性的生成 |
生成的連續性 |
|
時間性 |
時段性的單位 |
連續性的整體 |
|
變化性 |
不斷生滅(多) |
不斷變化(一) |
3.「意義論」:
(1)
「場有哲學」的意義論強調「境界開顯」,而所謂「境界開顯」指的是場有自身的意義開顯,也就是「場有宇宙相對於當下的蘊徼現行的開顯」。「蘊徼現行」是指一個當下的「虛機了斷」活動或事件,與場有宇宙形成「主客關係」或「景觀關係」(「觀」是「觀點」,「景」是相對於一觀點而呈現的境界)。
(2)
蘊徼現行與場有宇宙間的「主客關係」或「景觀關係」基本上乃是一個由異時因果(時間前後)與同時因果(空間前後)的時空結構所構成的脈絡關係。每一個當下的「蘊徼現行」或生命活動都是這個脈絡處境作為場有宇宙(永恆無限的場有自身)之活動作用的表現或分殊。換句話說,場有自身的永恆無限是在場有的造化流行(生成歷程)和在此造化流行的意識界面裡所開顯的意象世界中開顯的。
(3)
權能場有的三面終極性相:?「蘊徼真元」−權能場有永恆無限而絕對無斷的一面;‚「造化流行」−權能場有生成歷程不斷而斷、斷而不斷的一面;ƒ「意象世界」−意識現象的簡別外在、斷而又斷的一面。這三面性相互相涵攝、互相開顯,以此構成場有宇宙在自在層次上的境界開顯。
(4)
場有宇宙對人的境界開顯依存於場有宇宙自在的境界開顯,是較低層次、非本源性的意義開顯。
(5)
人是有靈覺性的場有者,人所了悟的場有終極性相就是場有真實在人的靈明中的開顯,也是反映在三面性相上:?「蘊徼真元」開顯於人的生命活動中;‚「造化流行」開顯於人所參與的權能運作裡;ƒ「意象世界」開顯於人的有執心靈中。
貳、比較哲學:
一、
「正覺」與「偏覺」
(一)六覺:場有哲學以「蘊徼真元」、「造化流行」、「意象世界」為場有宇宙的三面終極性相,哲學的全部覺解都源於此,但由於生命立場的限制,人所領悟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面,從本末整殊(完整/特殊)的角度可將其歸結為六種覺性−
|
1.
超切直覺
|
對「蘊徼真元」(場有本相、空相或無相)絕對無斷的覺性 |
|
2.
超切曲覺
|
對「造化流行」(場有行相、中相或事相)不斷而斷/斷而不斷的覺性 |
|
3.
超切執覺
|
對「意象世界」(場有末相、假相或物相)斷而又斷的覺性 |
|
4.
超切圓覺 |
對「場有自身」(場有整體性相)的覺性 |
|
5.
超切方覺 |
對「場有者」
(場有分殊性相)的覺性 |
|
6.
超切脈覺 |
對「場有處境」(場有脈絡性相)的覺性 |
(二)正覺:上述六覺本質上互相涵攝,統一圓融,是謂「六覺一覺」。這是本於場有宇宙終極和諧的圓融覺性,也是內在於一切意識而為人類智慧心靈本源的心性作用。能夠了解六覺本質上的統一,就是「正覺」,所以說「六覺一覺,謂之正覺」。正覺就其為心靈心識的本質而言是圓融周遍的,因為它乃是一個無偏頗,直接本於「太和」的覺性。
(三)偏覺:六覺統一作為「正覺」,是道德、哲學活動的最後根源,也是真理追求的「正根」,但人類哲學歷史上「正覺」從未成為現實,執著於一覺之偏而互相爭衡才是真實景象。這種「正覺分裂,偏覺爭衡」的現象,與哲學思想的型態或派別的對應關係如下−
|
偏覺爭衡 |
思想型態 |
哲學派別 |
|
1.直覺偏勝 |
突顯「蘊徼真元」之絕對無斷相 |
神秘主義、一元主義 |
|
2.曲覺偏勝 |
突顯「造化流行」之不斷而斷/斷而不斷相 |
變易主義 |
|
3.執覺偏勝 |
突顯「意象世界」之斷而又斷相 |
現象主義、分析主義 |
|
4.圓覺偏勝 |
突顯「場有自身」之整體相 |
整體主義 |
|
5.方覺偏勝 |
突顯「場有者」
之分殊相 |
二元主義、多元主義 |
|
6.脈覺偏勝 |
突顯「場有處境」之脈絡相 |
處境主義、脈絡主義 |
二、
東西哲學比較:
|
|
西方 |
印度 |
中國 |
|
偏覺爭衡 |
執覺、方覺 |
直覺、圓覺 |
曲覺、脈覺 |
|
意識心態 |
異隔 |
同獨 |
同融 |
|
理性生命 |
驚異型的外向知性衝動
(感異、驚異、立於異) |
驚態型的內向知性衝動
(感同、驚異、絕於異) |
關懷型的仁性衝動
|
|
智慧型態 |
外向控制型 |
內向控制型 |
感通直覺型 |
|
理性道術 |
形式邏輯(Logos) |
因明瑜珈(yoga) |
中和術 |
|
文明格局 |
動印文明 |
寂印文明 |
易印文明 |
1.
意識心態:
(1)
異隔:「感異成隔」,即意識心態把事物孤立起來看的傾向(「感異」),也就是「意識我」對非我和非意識的排擠,把自己視為惟一真實,等同於場有自身(「成隔」)。其結果是導致場有界的分裂和場有自身的遺忘,以及自我的不斷擴張、逞強爭霸和強烈的虛無主義。
(2)
同獨:「感同消隔而成獨」,即意識心態感同於異並竭力在異中求同,即使不能消除異隔也會對異之所在視若無睹,其極端發展是意識我的自我泯滅。
(3)
同融:「融中求同」,即意識心態承認事物之「有異有隔」,但「有隔而無礙」,即所謂「融」。同融的前提是「有隔」,而同獨則是「消隔」,這是二者不同之處。
2.
理性生命/智慧型態/理性道術:「不安而求安」−追求理想實現的生命
(1)
驚異型的知性衝動/外向控制/形式邏輯:西方文化之理性生命源於異隔心態,個體性是理性生命的的目的,形式邏輯是其理性架構的基礎。另一方面,此一理性生命為「知性衝動」所充溢(追求智慧),追求外向性的知能,以求控制外在事物。
(2)
驚態型的知性衝動/內向控制/因明瑜珈:印度文化之理性生命源於同獨心態,因明瑜珈是其理性架構的基礎。此一理性生命同樣為「知性衝動」所充溢(追求智慧),但追求內向性的自我返回,以求控制內在自我。
(3)
關懷型的仁性衝動/感通直覺/中和術:中國文化之理性生命源於同融心態的仁性關懷,中和術是其理性架構的基礎。「感」指生命同體的感情,「通」指生命的通順、無礙,以生命同體的感情來成就生命的通順、無礙,是謂「感通」。生命的通順就個體而言就是「中」,就群體而言就是「和」。
3.權能三印:即動印、寂印、易印
三、
「超切中道」的哲學架構:
|
場有哲學的真理論 |
六相一相,超切實相 |
|
場有哲學的方法論 |
六觀一觀,超切如實現 |
|
場有哲學的心性論 |
六覺一覺,超切正覺 |
|
場有哲學的工夫論 |
緣命復性,自誠致曲 |
|
場有哲學的超切中道 |
偏為正用,綜合得宜 |
參、生命哲學
一、根身性相學
1.
根身性相學:即泰古人自我反省其根身(即身軀)生長變化的基本性相的學問,是人類對場有本質的原初體驗形式,更是權能場有分析與實存生命分析辯證結合的關鍵點。
2.
場有本質的「斷」與「不斷」,在易經是以「―」與「−−」來象徵,唐氏認為「―」代表根身的無斷,即直立起來的身軀;「−−」代表根身的可斷,或彎曲狀態下的身軀。泰古人類透過根身的直曲活動,體驗出「斷」與「不斷」的真理。這種原始混沌的意識,沒有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分離對立,是宇宙與心性的合一,是人類對場有本質的最純粹、最樸實的體驗。
3.
唐氏解釋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人類最原始的場有經驗,「道生一」代表從原始的混沌意識發展為完全認同於根身的意識,是一種「無對而有我」的意識,即意識完全認同以根身為「我」,亦以環繞著根身的一切人物為「我」;「一生二」代表從「無對而有我」的意識發展為「有對有我」(二)的意識,將根身與周圍環境分別開來;「三」代表站立起來的根身,「二生三」便是以此站立的根身為座標,將「我」與世界、主體與客體分離對立,也形成以根身為座標而產生的對立−上下、左右、前後、陰陽、進退等;萬物和意義世界的開顯乃是以「立於三」為起點的,所以說「三生萬物」。
4.
「直詮」與「曲詮」:泰古人反省其根身生長變化的基本性相所運用的自然語言,能直接表達人類的「核心現象」(即人類存在的的本源−包括意義世界、道身、問題心、理性道術與精神人格的開始,唐氏稱為「一本」),稱為「直詮」;「曲詮」則是指用間接的方式,如神話、宗教、禮樂、儀式、文學、藝術等,來暗示根身的生長變化。「直詮」與「曲詮」,唐氏合稱為「二軌」。
5.
「雙向」:泰古人原始樸實的體驗裡,存有乃是一個混然無間的真理與真實(所謂「超切直覺」),但隨著文明進展,有間的「自我意識」逐漸形成,泰古語言也開始向「自我」觀念和「大我」觀念分化發展,此即所謂的「雙向」。「自我」觀念的發展成「我識透視、知解理性」的絕對化,導致文明人的孤立無根,所謂「斷根異化」。文明人一方面在「自我」觀念下「斷根異化」,另一方面又有意識或潛意識地向「大我」作「回歸尋根」的努力。
二、人性論
1.「仁材兩極」:人性的衝動就其感於存有本性之「斷而又斷」而言是「愛羅」(eros),就其感於存有本性之「斷而不斷」而言是「良知」。「良知」就是人的「仁性」,「愛羅」是人的「材性」,「良知」與「愛羅」構成了人的主體性的「仁材兩極」。
2.「公道原理」:生命權能無論通過「仁性」或「材性」都有自求實現、自求滿足的本然傾向,即所謂「自誠自直」。自直而得直(求滿足而得滿足)就是「公道」,不得直(求滿足而不得滿足)就是不公道,唐氏認為此「公道原理」才是道德的本質。
3.「曼陀羅智」:一切生命都是方中求圓,在不公道中求公道,唐氏稱為「曼陀主義的理性觀」,又稱「曼陀羅智」。
4.「克犧結構」:即生命權能的自克與犧牲。生命在不公道中求公道,必然面臨某些內在矛盾(特別是「仁性」與「材性」的對抗),也必然要有所取捨,這時便需要自克與犧牲,來成全公道原理。
5.
西方傳統的「克犧結構」,是以阿波羅的清明來克制戴奧尼索斯的狂妄,成就了知解理性而虧負了本能欲望;尼采和佛洛伊德等近代哲學家則將愛欲與知性等同於「愛羅心性」之一部分,主張不能靠壓抑愛欲來成就知性,而須以昇華代替壓抑。但即使如此,在唐氏看來,西方哲學仍然不脫成就「愛羅」而虧負「良知」,僅是「半邊人性論」。
6.
相對的,中國傳統哲學以「仁性」為主體,「克犧結構」基本上是以「德」(仁性)統「福」(材性),成就「良知」而虧負「愛羅」,也是「半邊人性論」。
7.
唐氏主張「仁材並建」才是完整的人性論,良知中有愛羅,愛羅中有良知;良知是偏向無斷與互體性的愛羅,愛羅是偏向有斷與自體性的良知。
8.
唐氏分析儒家「仁性」的三層次:「本體之仁」、「類性之仁」、「道德化仁」
(1)「本體之仁」:對一切存有絕對無差等,絕對一視同仁的愛。
(2)「類性之仁」:又稱「本能仁性」,是本體之仁在人的類性稟賦限制下所本具的同體感通力量,是人類在仁性方面最自然的良知良能,也是一種「私仁」。
(3)「道德化仁」:是仁性的道德化或社會的理性化,亦即是本體之仁通過本能仁性的中介作用在社會法制和倫理規範中進一步的落實。
9.
近代中國哲學家人性論的演進
(1)
中體西用:張之洞首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西學愛羅本體的人性論並無認識,他們所了解的「仁材並建」就是「良知」與「愛羅」的簡單相加。
(2)
良知自我坎陷:由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所提倡,仍是站在中學本位,以「良知」為主體,「仁材並建」就是「良知」往下轉,以轉出「愛羅」。
(3)
場有哲學:唐氏的「仁材並建」,乃是把「愛羅」從「良知」的壓抑下解放出來,使「良知」與「愛羅」同有相等的本體地位。
肆、結語
成中英將當代中國哲學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
階段 |
代表人物 |
特色 |
弱點 |
|
一 |
梁漱溟、熊十力 |
為中國哲學作不遺餘力且意涵深奧的辯解 |
欠缺對中國傳統進行批判…探討及檢視;對西方應有的完整全面且細緻精密的了解亦付闕如。 |
|
二 |
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
為中國傳統融鑄新型式同時注入新生命 |
與西方之間仍然缺乏完整的溝通及往還 |
|
三 |
唐力權等 |
中國哲學已溶入西方哲學思考的格局中開始流衍 |
|
唐力權之所以能成為第三代人中的佼佼者,不僅在於其廣博的哲學資源和強烈的體系意識,更在於其不偏不倚、從容中道的氣度和慧識。當然,「場有哲學」也僅是一個前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