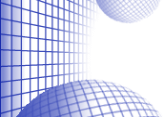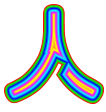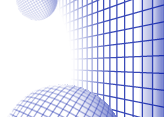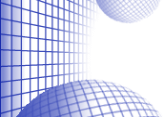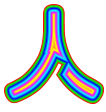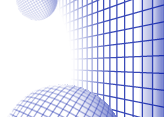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
(一)
談論神秘主義,這個行動本身就帶著悖論。可以被我們拿出來談論的,就已經不是神秘主義了。亦即,我們的主題雖是神秘主義,但我們所用語言談論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神秘主義,我們無法避免這個矛盾。不過,這個悖論亦反映在歷代神秘主義者自己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這些神秘主義者,對邏輯的發展提供了最大的貢獻;他們的思想著述呈現出極高的論證性格,嚴謹得令人驚訝;而他們所用以描述上帝的各種比喻和語式,其豐富繁華,連最富想像力的非神秘主義者亦難望其項背。就此而言,嘗試去用語言反思神秘主義,至少不是一個完全非法的事情。
但不論言說藝術如何超絕,至終任何神秘主義都歸入某種不可言說的境界,這種境界不是向外的追尋,而是往內心深處走去。我願意說,向內心尋找,是當代人尋找上帝的唯一出路,至少對基督教而言是如此。但提出這個命題,必須很小心的來理解,因為我底下要論證的就是指陳一種『直指內心』、當下體悟那『不可言說之奧秘』的進路的無奈,並勾勒出一條迂迴的走向內心之路,因此,我的『向內心尋找』並不同於傳統的神秘主義,也許可說它源自於基督教中的神秘主義向度,但它對以往的神秘主義是具批判性的。
素樸地說,我們無法在教堂中找到神,無法在某個既定的物質性場所找到神,畢竟舊約時代已經過去,錫安山不再,聖殿不再,我們還可以在那裡找到上帝的蹤影呢?讓我們永遠記得耶穌的話:『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約14:16-17)使得我們今天仍得以看見上帝的基礎就是聖靈,而我們與聖靈的關係是一種內在的關係,這截然不同於舊約的先知與上帝的關係、或使徒們與耶穌的關係。也許可說,正是聖靈論開啟了神秘主義的可能性。
以聖靈作為向內尋求上帝的論據,這是從神學一面來說的。然而,還可有另一向度的論據,此一向度尤其展現在二十世紀歐陸哲學對主體性的關注上。當胡塞爾建構現象學時,他致力於對主體性的闡明,將一切對客體的知覺都放在主體的意識之中來處理,由此超越了單純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現象學的思潮襲捲了二十世紀,可以肯定的是直到下一世紀,都會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向度,並且將會有更多的學者嘗試以現象學來說明各種宗教經驗,尤其是宗教經驗愈益趨向人的內心經驗。由此,對宗教現象的考察,我們雖不知最後會得到什麼結論,然而至少在出發點上,我們的方向是向內的。
在向內尋找的各式努力中,基督教傳統中的神秘主義給了我們極豐富的資源,但神秘主義的進路所隱藏的危機是以神秘體驗作為達於上帝的『真正進路』(至少在境界上是最高的),加上其極端的個體性,從而很容易走向一切同一的結論。
幾乎所有的神秘主義都以某種不可言說的至高奧秘作為對神聖最終極的表述,而且都具有一個特徵:強調這個至高奧秘的獨一性。由此,任何宗教,只要談及這個至高奧秘時,很容易走向一種任意的普世性斷言:佛教、回教、基督教、老莊、儒家等所談及的終極的信仰對象,都是同一的,各種宗教不過是同一個真理的不同展現,各種學說至終所想說的乃是同一個對象。正因為此一至高奧秘乃是不可言說的,所以任何言說都只是它的一個反映,而各種宗教裡的最高境界,那不可以言語道詮的境界,也便因此而是同一個至高奧秘。
由於二十世紀各宗教間的多元交流,使得這種傾向漸漸被突出,從而凡是宣稱某一宗教信仰對象乃是那唯一最高奧秘者,皆被視為獨斷、不寬容、守舊、不敢面對衝擊。但『真相』究竟如何呢?是同一還是差異?我將嘗試在另一篇可能會流產的文章中再討論這個問題,時至今日它顯得十分重要。首先,若我們仔細思考,便會發現無論是主張自己的宗教是獨一真理或各宗教都是同一真理的呈現,這都是一種趨向同一的作法,只是對這同一真理的發言權有著不同理解。但這是唯一的選擇嗎?後現代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要破除這種作法,它稱其為邏各斯中心主義,亦即,這種趨向同一的作法乃是源於希臘哲學中對作為宇宙萬物原理的邏各斯的尊崇,但今天我們已不再能如此素樸地肯認的確定存在這麼一個統括一切的原理,儘管我們也不應該素樸地拋棄它。
(二)
那麼,難道要走向差異嗎?這一樣令人不安,因為一不小心就會掉入絕對的多元性與相對性中,從而任何同一的可能性都被抹消,它唯一的下場就是虛無主義。(嗯,雖然這個斷語顯得說的太武斷,但我仍想以先知的心情來給出這個斷語。)對此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態度:或是勇敢的接受、或是無奈的接受、或是智慧的抵抗、或是愚頑的抵抗。然而,在此要下任何斷言都顯得太過倉促。無論在神秘主義中的至高奧秘究竟是一直為各宗教所共同信仰與言說者,還是僅為某一宗教所壟斷,還是僅是一個天真的幻想,都是要先放入括弧的。
把問題拉回神秘主義。在神秘主義中,這種以某一至高奧秘來統一各家的做法是世紀末面對宗教四興、學說紛陳的局面,最常見也最受觀迎的處理模式。我們可以看到諸如被稱為神話學大師的坎伯正是採用這種方式,將多元的現象統一在某一系統建構之中。這正是我在此要批判的。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各種不同的宗教現象,其間的確有類似處,但把差異處歸諸民族、文化、地域等偶然因素,而把類似處抽象出來再加以理性構造,以成為一套看似合理的解釋系統,以此來說明多元宗教現象的背後根基,同時嘗試以此來向那推動著各不同宗教的同一真理本源靠近。這種看似超越一切宗教各式獨斷教義宣言之上的持平作法,其實本身亦是一個獨斷的宣告。如果堅持現象學精神,那麼就要堅定地否定一切任意為之的理論建構,不論它看起多合理、多能前後一致、多能加以實證、多能說明並預測宗教現象。
這種任意統一的方式是一種獨斷的宣告,更是一個走捷徑的宣告。把一切人類可言說的東西放在一邊,從而突顯其對立面並以此作為某種存在的最終基礎,這樣做並不就提供了任何積極的知識,亦即,並不就揭示出真理。生於康德之後的一切宗教學工作者,都應該嚴肅地面對康德指出的限度,任何可靠的思想,都僅是奠基於吾人的可能經驗,不以經驗為基礎(但非僅限於經驗)進行的任何玄思,都將面臨相對化的挑戰,亦即,將無法面對以心理學和社會學說明宗教現象的挑戰,從而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就是陳服於這個挑戰而坦然地以心理學和社會學合理化宗教現象,從而將一切宗教思想都視為相對,並因此而取消任何神秘主義;(關於此點,我們可以想想坎伯對神話的解說模式,雖然也許他不會承認他的作法事實上是取消了傳統意義上的神秘主義。)另一條就是獨斷的固守在自己的宗教中,成為一個基要派信徒。(我們可從當今基督教、回教、和各式的基要主義中看到這種固執的作法,並看到這些基要主義在當代的復興,對我而言,這種復興對世界的影響是負面的。)
如果不願成為上述的任何一類,就讓我們回到起點。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不同的宗教現象,這些現象本身就有它的意義,任意的將其中某些特徵抽象出來並弭平其他特徵,這種作法適足以破壞對單一宗教現象的嚴肅考察。倘使這種抽象和弭平的理由是指經過各不同宗教現象的對比而得出,那麼就有必有質疑:對比研究的目的是要得到同一性還是差異性?就人文現象而言,對比研究最後應該走向的目標是呈現差異,而非呈現同一。但這並不就表示放棄對同一性的追求和信仰,只是指出在當前多元處境中如何聯繫成對話共同體,至於對話的結果是否可能走向對同一至高奧秘的肯認,或者走向對某一宗教言說體系的獨一信仰,或者是承認差異與彼此化約的不可能,這些也許都不應是在對話之前就該先設定好的。
把多元宗教現象統一起來的做法,看似能夠超越各種地域文化的偶然因素從而作出某種看似客觀的斷言,這只是一個取巧的手段。這類斷言本身難道不也是在某個時空背景底下作出的嗎?在此這種作法一樣不能逃脫它所欲克服的困境。多元性自然導致相對性,但要超越此一相對性,需要進行嚴謹而緩慢的工作,隨意地以統一多元現象來克服多元性從而形成一新的單一性,這與各種宗教立基於其自身傳統而作出的單一性宣告其實相距不遠,同樣都是獨斷地趨向同一。現象本身是唯一的出發點,在此應該拒絕對這些現象進行抽象理性構造以便說明其相對性成因的任何嘗試,這種理論構築本身就要被批判。對人文現象的描述要謹慎地避免來自於任何理論預設的因果說明,尤其是那種素樸地以某個『不可言說的至高奧秘』作為最高預設出發而形成的說明。無論這種說明本身看似多合理,其方法建構就已是有待商確的了,而且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事實上這種看法從未能真正解決問題,相反的卻更多地成為了一般人逃避誠實思辨的藉口。
(三)
對於此一『不可言說的至高奧秘』,我有一個建議:它只是一個界限概念,而非實體概念。我想論證,這個概念只標示出人類理性的界限,但在它之後,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對我們而言只會造成徒然的爭論。因此對基督教來說,我想建議的方向是:放棄對那位『不可言說的上帝』的爭論,轉向面對『可言說的上帝』的面容。我們當然是信仰一個實體而非一個界限。我們所信仰的就是我們所能夠言說的,至於那之後不可言說的某物,則應被放入括弧,對它不僅不能言說,亦不能信仰。對任何事物的任何信仰,至終都是一種言說、一種語言行為。
在此可能會有疑慮:上帝的奧秘性不會因此而被取消嗎?但這個疑慮的產生不過意味著未能弄清我的作法的真正意圖,我並不設法也不可能取消上帝的奧秘性(相反的在下幾篇文章中信仰的奧秘性將被突顯),而是嘗試開出一條可供對話的道路,因為誰想在對話中呈現上帝,誰就必須盡全力去言說可供言說的東西,而避免言說那不可言說的東西。試圖言說不可言說者,至終都只是言說到某個幽靈,這種東西無法在對話中呈現,不能在人和人的交往中被看到,而不能在人際交往中呈顯出來的,即是不能在生活世界中呈顯出來的,從而也就對於信仰──這麼一個具有群體向度的現象!──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
把上帝與那在神秘體驗中所經驗到的不可言說的至高奧秘等同起來,也許是一個錯誤。上帝是一個奧秘,但祂是個可言說的奧秘。凡屬祂不可言說的部分,通通要被放入括弧,擱置不論。若仍依神秘主義傳統,企圖以各種語式來類比、靠近這位不可言說的上帝,必然會陷入各種宗教間沒有同一立足點的爭執中,對於這樣一位上帝,對我們來說沒有意義。『不可言說者,就是不存在者。』補充的命題是『尚未言說者並不等同於不可言說者。』我人所要進行的工作就是『言說那尚未言說出的東西。』我大膽的提出這幾個命題,作為對整個神秘主義傳統的總結和展望。在其中,尤其是第一個命題,很容易讓人認為我只不過是在重覆維根斯坦的話,並且會藉用晚期維根斯坦的自我批判來反駁我的建議。我自知無法逃避這個質疑,並會試圖(如果有必要的話)在往後的文章中澄清我的真正用意,而此刻之所以並未指出,是無能而非不願指出。
以上幾個命題需要一個非常必要的補充,沒有了這個補充,這些命題就會被徹底誤解。當我說『不可言說即不存在』時,絕對無意把它用以描述實在現象,若是如此,我將從根本上否定任何形式的神秘主義,從而也否定了我自己的信仰。這些命題是作為一種方法上的懸置而提出來的,亦即,我要用這幾個命題來懸置一切獨斷的宣告,視其無效,並尋找一個可供言說與對話的出發點。這樣的作法讓人想起笛卡兒和胡塞爾,沒錯,當我這麼做的時候,我的頭腦裡的確閃爍著他們的洞見,並且樂於承認我繼承了他們的精神。
對於把上帝劃入『人類所不可理解的奧秘』之中的做法,我已感到有些厭煩了,這個有其深遠傳統的做法於今已成為了一種逃避的理由,它除了顯示出任意的理性規避外,似乎已失去任何積極的意義。『預定論』是一個奧秘嗎?『自由意志』是一個奧秘嗎?說它們是奧秘從而是人所無法理解的,這就解決了問題並讓發問者心服了嗎?從某個角度來看,我提出『不可言說者,就是不存在者。』這個極端的命題,只是對『上帝是不可理解的奧秘』這個命題的另一種表述,儘管表面上看起來它們是彼此對立的。我在這裡想做的並不是想動搖所有神秘主義(乃至於所有宗教!)的根基,正相反,這個命題所要做的乃是剃除一切偽裝的、輕鬆的、走捷徑的神秘主義,並由此還原出神秘主義(但非那至高奧秘)的真正基礎。至於會得到什麼東西,自然不可能是這幾篇文章就能給出的了。
此一處理模式首先面臨的可能責難就是相對主義。當把一個至高的、可說明一切的原理(至少在方法論上)取消之後,對各種不同宗教現象、宗教學說所呈現出的多元與紛雜,就很容易將其視之為各種不同的世界觀而已,只是因為處境不同而形成的不同世界觀本身。但是,若能將以上處理模式的基本精神貫徹到底,則便可以避免這種詰難,因為這種將多元現象視之為不同世界觀的反映,一樣是一種任意的統一多元性的作法,只是這種作法較之以往不再具有宗教性罷了,或可視為某種解神話的過程。
我想以另一種方式重覆以上的論證,以讓它們可以更清晰地被理解。我問:是否以一個至高奧秘作為統攝一切的終極原理,就可以超越相對主義可達到『絕對』與『客觀』?難道事實不正是:各個宗教學說間對此一至高奧秘之發言權的爭奪,導致了相對主義的詰難嗎?為何這個至高原理要屬於這個宗教,而不屬於那個宗教?難道不正是因為它的不可言說性導致任何宗教學說都無權宣稱它的信仰對象就是這個至高奧秘?也許尚可辯稱:儘管各宗教所言說者不一,但只要各宗教徒夠開放、夠謙虛,能夠承認其他宗教亦是真理的一部分,那麼吾人就依然可以說是信仰了同一個至高奧秘。這樣的辯稱最易為現代人接受,基督教中的自由派信徒最樂於承認這一點並據此而視其他基督徒為獨斷與蠻橫,然而它事實上卻是把對至高奧秘的信仰建基於共識之上。(這個共識就是:『有一個』至高奧秘超越了所有人的言說。)姑不論『大家都承認』這個天真的希望是何等看不清現實,把信仰建基於共識的作法,看似能夠在當前世代超越一切相對主義而達致絕對,然而這同時意味著下一世代的人們隨時可以改變這個觀點,只要共識能夠達成。如此,把此一作法放在歷史中來看,一樣是一種相對主義。不過,我並非要反對這種基於共識的相對主義,因為在相當程度上我自己的處理模式也是以共識為基礎,在此我要批判的是這種自認為可以超越相對主義的作法本身就是相對主義式的。
(四)
問題並未就此解決,似乎我也不過是在貫徹一種絕對的相對主義,拒絕任何至高統合原理的嘗試。(儘管用『絕對的相對主義』這辭來統括我的作法,似乎也是一種統一多元性的手段。)無論如何,當我把作為同一性保證的『至高奧秘』懸置起來並承認多元宗教現象各有其意義後,『相對』、『主觀』、『沒有標準』這些帽子還是很容易戴上,尤其對基督教來說,面對當前各式強調內心體驗的新興宗教,彷彿重新強調基督教的『獨一』、『客觀』、『唯一標準』是一條唯一可行的路,但我認為這條路依然有斟酌的必要。
我反對為了突顯基督教的獨特性,便把基督教的『歷史客觀性』、『合理可證性』搬出來,與其他宗教或新興宗教所強調的內在體驗相對立。我認為一旦我們如此做便將模糊了新興宗教與基督信仰的真正衝突點,並重又陷入二十世紀哲學所大力批判的自然主義和歷史主義的預設中。(我並不說陷入自然主義與歷史主義,而說陷入其預設,是因為基督徒不會真正同意自然主義和歷史主義,然而卻經常不自覺地分享了它們的預設,例如對基督事件的歷史客觀性的極度強調、對創世神話堅持以歷史事件來看待、對聖經詮釋以字面意義與詮釋的自然性作為基本的判準等等,從而總是讓自己陷入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若我們依然把對內在體驗的關注與『主觀』等同起來,而以此強調更有價值的『客觀』,我們就依然停留在十九世紀前的水準,而完全達不到整個二十世紀的思想所已走到的高度。這除了讓神學家的職份在學術界被看輕外,也將讓我們無能面對新興宗教的衝擊,更何況於今後現代主義已走到連主體都拋棄的地步,我們還停留在素樸地主客二分的層次,對話將如何可能呢?
我當然不是說強調主體性就夠了,但這是一個必要的起點,沒有從主體的視域出發來呈現(信仰)真理,就沒有真正的基礎。甚至說得極端點,沒有關注主體的向度,就不可能看清真理。作為起點,主體性的向度值得我們關注,就此而言,當代大興的『心靈宗教』乃是一個契機,它毫不留情的批判了傳統基督教對主體性所未給予的應有關注。這對基督教來說,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轉機,但在轉機之中,有著被混同的危險,這尤其展現在靈恩派中一些較缺乏神學反思的教會一味追求神蹟奇事的狂熱表現中。更重要的是請我們看到自己那些應該修正的偏見,客觀歷史性絲毫不能保證信仰真理,強調內心體驗並不等同於強調個體,群體依然在這裡找得到它的位置,而且是很重要的位置。
奧古斯丁說:『不要往外奔馳,回歸你自己的內心吧!真理就住在人的內心。』很有新時代的味道,對不對?但新時代所強調的,不必然就是錯的,相反的,作為這個時代的精神,新時代講出了人心深處的某些東西,這些東西在基督教傳統中也可以找到,而且極為豐富,然而我們卻自己把它們丟失了。但這種聲音一直未在基督教中缺席,僅就當代新教神學來說,布特曼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也許我們去應該更專注地去傾聽這些提醒。
因此,我寧可冒著被指為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危險去進行這個方向的探索,並且希望能夠有力的給出證明:我不是一位相對主義者,也不是一位懷疑主義者,並且,在最終意義上,我是一位信仰基督之上帝為人類救贖唯一希望的基督徒。
但什麼叫回歸內心?像神秘主義者那種方式嗎?如果想要避免任何簡單的同一或相對,那麼,這條回歸內心之路,就因該經過迂迴,我稱其為『他者的迂迴』。於此,我回到了我在這篇序言開頭所提出的構想,底下我將嘗試勾勒出這一條路的進程。
回 [神秘主義]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