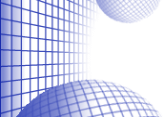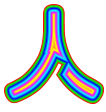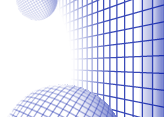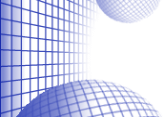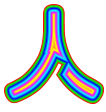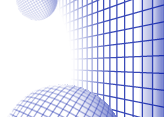看了台大哲學系教授關永中的《愛與死亡--與馬賽爾懇談》很有體會,所以想要在這裡整理他的文章。
對有愛的人而言,死亡並不是一個陌生的領域。愛與死亡,至少在一個
共同點上是吻合的:那就是--我不再為自己保留什麼!站在愛的觀點上
說,愛者在忘我的給予中置生死於道外;而站在死亡的角度上說,它使愛的
徹底付出成為可能。在人生際遇裡,蠶繭消逝,飛蛾出現,愛情透過死亡而
獲得昇華,黑夜退隱,曙光初露,愛者經歷死亡而獲取永恆。這使得我們想
到《雅歌》裡寫道:愛情強烈如死亡,洪流不能將它熄滅,江河也不能將它
沖去。羅洛梅也說:愛情是死亡與不朽的交會點。乃至於馬賽爾能夠說出那
句扣口人心弦的名言--「去愛一個人,就等於對他說:你永遠不會死!」
這句名言出自馬賽爾之戲劇《明日之亡者》。這句名言蘊含了馬賽爾哲
學的精隨,深究其意,它至少蘊藏著下列幾種意義:
- 死亡不能終止我對你的愛
愛本身就蘊含著不變的忠信,與無條件的承諾,承諾著不論順逆、
貧富、健殘都愛你到底,至死不渝。為此,馬賽爾在他後期名著《人性尊嚴
的存在背景》中有這樣的提示:愛,從其最具體的意義下而言,……似乎奠
立在一無條件的基礎上,即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始終如一地繼續愛你。字裡
行間寓意著,深厚的愛不因生離死別而中斷,或有所改變。
- 你至少活在我的記憶中
愛者的死亡所引致的打擊是莫可言明的,在悲痛之餘,他的遺物、
遺言、音容、往日同在的時光片段,都突然變得珍貴起來,並企圖抓住對方
昔日的聲音容貌,留住對方的愛與親在。假如在記憶中超越了時空的阻隔,
越過死亡的鴻溝而與已亡的愛者重逢,那無論是在夢裡,還是在冥想之中,
彼此仍會如同閃電一般馬上地把對方辨認出來,彷彿未曾分離過一般。
- 我在愛中體會你的臨在
在相愛中,愛與被愛者的心靈彼此契合,兩者彼此在心靈上有感
通、共鳴、交流與結合,兩個生命因愛而融合為一個整體,一個圓,這就稱
為愛的「臨在」。愛者的「臨在」已超出了肉體上的接近,形體的接近與否
已經成了次要的因素,此後不論生離死別,都不能阻止愛者在心靈間彼此的
臨現。
- 我在愛中體會你的不朽
愛,就是祝福對方獲得幸福圓滿,渴望對方永恆不朽,如果相信這
一切都只是終歸烏有的話,我們還有勇氣去珍愛一切嗎?我們拒絕愛者的死
亡就是毀於絕對的空無,反而愛者的存有跨越了肉體死亡的藩籬,當我們在
愛內確信被愛者的不朽時,這份確信自然會容許我們體驗已亡親友之臨在與
恆存,或者說,愛的願望、確信與體驗,會使我們在內心裡聽到彼岸的呼
喚,真切地經驗到對方的心聲與祝福。
生命與死亡彼此蘊含著,生是一個有死的生,死亡是使生命可能的先驗
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的愛都有著一種基本的傾向:即完全地跳出自
己,為造就對方而鞠躬盡瘁,在忘我的犧牲中投奔那愛的本源,在顯然地愛
一個人的個體中,隱然地愛著那在人內作為人的根基之「絕對的你」。如果
換著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愛的徹底付出,可以在死亡的一剎那中實現,
當人們連自己的形軀都要告別,他已沒有什麼可讓自己去再佔有,他可以毫
無保留地跳出自己,為所愛者做一個全然無私的奉獻,此時,愛者不再返回
自己,而在越過死亡的鴻溝當中,成就了最徹底的付出,也就是說,徹底的
愛是死亡與永恆的交會點,而同時成全於忘我的付出之中。
【附錄】關於過去--包容,抑或是憎恨
文/sinner
沙特說:「擁有過去的,僅僅是那些在其存在中與過去的存在相關的那
些存在,也就是那些要成為他們自己過去的存在。」人在走向死亡的一生
中,不斷地一點一點地把自己的過去拋到後面,只要他沒有中止生命,他就
總是要不斷地成為他的過去,成為他過去的總和。死亡則在最後確定了他,
把一個人的一生整個變成了過去,這也就最後地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一個
人的本質。
沙特於一九四四年發表的著名劇本《禁閉》也體現了他這個思想。加爾
遜生前是個臨陣脫逃的懦夫,他一直想擺脫自己總是被視為懦夫的角色,但
是不可能,因為他已經死了,他的命運已定,本質已經不可能改變了。但是
在劇本裡,他又會說話,還活著,這是因為在劇本裡,死其實是生的一種方
式。只不過在別人眼裡,他的死,永遠改變不了人們對他的看法,所以他
說:「我死的太早,人們沒有給我留下時間讓我澄清。」劇中另一個主角則
說:「人們總是死的太早,或者死得太晚了。」
沙特的文學作品中,幾乎沒有什麼肯定的東西,他否定既定的一切,否
定自然,甚至包括其自身,尤其是「過去」的無法改變讓他憎恨,他曾經說
過:「我憎恨我的童年,憎恨由它而來的一切………人的童年造成了不可超
越的偏見。」於是,沙特帶著一種否定的立場,卻要試圖努力超越過去,要
人們向著未來進行自由選擇的行動。在沙特看來,真正值得嚮往的、值得肯
定的美好東西,只存在於另一個世界--即想像的世界中,人的自由選擇行
動實際上就是對過去與正在變成過去的現在的否定。人是孤立無援的,只有
依靠自己的行動才能夠通過超越世界與超越自我的道路。但是最後,他還是
認為:外界是不可改變的,人永遠達不到理想的自我的永在,而且人與人之
間的衝突是不可調和的;或者說,不管在想像的世界裡如何地自由行動,沙
特還是無法抹去過去--他那一段憎恨的童年。
沙特出自於否定的立場,揭露了時代的混亂,這使得他的文學作品具有
十分強烈的吸引力與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在沙特看來,外界的一切都應該否
定,一切都是醜惡而混沌的,就算是自然環境,在沙特的筆下也絕無可愛之
處,那只能引起人的厭惡。這是他與卡謬作品的重要區別:卡謬也具有強烈
的否定精神,但是這位才華洋溢、不幸早逝的作家卻肯定那美好的大自然-
-迷人的陽光、遼闊的大海以及美好的懷念,為了這,人們應該對生活回答
「是」,像西西弗斯那樣帶著荒謬的遭遇,卻還是窮盡今天,盡可能的生
活。沙特把希望寄託於未來,實際上是寄託於想像的世界,而卡謬則把希望
寄託於腳下,不相信什麼虛無飄渺的明天、來世。
在哲學上,他們對於「過去」都有同樣的看法,可是,他們之間最大的
差別卻是,他們包不包容自己那充滿誤謬的過去,願不願意在當下也包容自
己所面對的世界。在我看來,對於那些無法改變的,人們必須做下決定:包
容,抑或是憎恨。
參考資料:《一個絕望者的希望》,杜小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