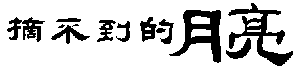4.透過大自然抒發不平。
這第四種對大自然之音的詮釋, 就有強烈的人之主體性格的出現。
譬如說箏曲「寒鴨戲水」,若只取題,一定馬上想到在水中逐戲 的鴨子。但按原版,曲速三變,由三版、二版到烤拍等三個先慢後快 的段落,這種速度對比,加之「重三調」端莊深沈的調式,分明是在 對人生作一種嚴肅的思考,而且心有所感不得不吐的成分很重。
國樂一如詩,往往借景喻情。標題寫景,音樂卻寫情。
這類的借景喻情, 人之作為主體就很明顯的浮出於大自然,成 為音樂的主角。
大自然,不過是配襯而已。甚至可以說,大自然反過來融入了人 之意志與情感。類似的曲子,還出現於古琴曲「幽蘭」、借蘭描述鬱 鬱不得志之感慨,或琵琶曲「<大浪滔沙>」,以其最後長輪轉入低音弦 的滑揉並雙音,呈現心未能止的感慨,是標準的借景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的蒼涼心境。
當然,華人音樂中,還有很多節慶婚喪的曲調、或描述民間生活 色彩的諸多曲目、或宮詞閨怨、或千古離情,但這都完全以鋪陳歷史 、社會、人世、情感為主的,並不涉及自然景觀,而這類曲子要不就 鑼鼓喧天熱鬧非凡,要不就是哀怨的獨白,彷彿用樂器把蒼涼哀怨唱 給一個無法改變現狀的、充滿無力感的對象。
所以我們會發現,像貝多芬六、七、九交響樂這樣人之作為主體 非但不融入自然,甚至刻意強烈的浮出於自然之外、並與自然對抗的 音樂描述,或者像如貝多芬後期音樂,在自然之上另有「他者」作為 主體,人與「他者」直接產生對抗、控訴、吶喊祈求,或人邀請「他 者」進入陪伴觀照己心的音樂描述,可以說,完全不是華人文化的基 調,當然,也就很難在華人的藝術中找到對應了。
(請參「從走進大自然的悲劇英雄到向「他者」吶喊對話的凡人——貝多芬音樂中「自然」的過渡地位」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