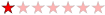[星球考古誌] 宋史報告
版面規則
[星球考古誌] 宋史報告
昨晚睡得遲,四點上床時仍無睡意。在床上翻來覆去,突然想到明年畢業後,小小的房間怎麼裝的下研究室多達兩大櫃的書和研究報告、期刊論文。這讓我興起了清理書櫃的念頭。雖然櫃子裡的書很明顯都是自己覺得有用的,但翻一翻,或許可以再清出一些大學時期留下、現在已經無用的講義。只是沒想到幾個資料夾裝的都是自己之前蒐集來的資料,談集郵的、一些難找的歌詞、還有一些有助於記憶單字的英文字根的講義。翻了五六分鐘,決定要丟的大概只有一本民國八十幾年的犯罪預防研討會論文集,那是四五年前政大社會系辦要從山上的季陶樓遷到山下新落成的綜合院館大樓時出清雜物時,撿回來的書之一。裡面的文章和我有興趣的領域相距甚遠,就丟了吧。
櫃子裡有一本標題為「歷史報告集」的報告夾。記得是大四、大五時,將自己在修歷史系的課時寫出的報告裡,挑出一些自認還不錯的彙整起來。雖然就一直擺在每天都會瞄到的櫃子裡,不過這幾年一直都沒去翻。決定以社會工作為主修後,唸歷史就變成躲在我心裡的一個「不醒的夢」。喜歡歷史和自己喜歡文學一樣,即使在閱讀時能感到自己心裡的熱情,不過充其量也只能在自己到書店買書時,多增加這些書的購買、閱讀比重來滿足。翻著這本報告集時,過去上課的情形重新浮上腦海。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宋史」這門課。在大一進歷史系時,就聽說修「宋史」等於「送死」,因為老師除了上課指定必讀的資料遠超過現在大學部的課會唸的份量,每個禮拜還要就讀的東西寫出一篇報告出來。那學期除了修了二十九個學分,每個禮拜還要花一天的時間實習,儘管辛苦,卻也是我大學五年來最快樂的一個階段。
以下十一篇報告,是我在大四修「宋史」這門課時繳交的閱讀心得。雖然現在已經記不太起那時學到了什麼和宋代有關的知識,但涵蓋各個主題的十一篇報告,每篇字數至少兩三千字,是我在某個學習過程中留下的紀錄,也是我心裡其中一個不願醒來的夢。
歷史上的宋朝
宋初政治
兩次變法
靖康之難與南宋政治
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宋代家族
婦女
城市、貿易、工商業
農村、土地、租佃
新儒學的興起
宋代宗教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一] 歷史上的宋朝
[b][size=150][color=blue]歷史上的宋朝[/color][/size][/b]
一般史家認為宋朝(北宋,西元960年至1127年;南宋,西元1127年至1279年,兩宋合計共320年)是中國近世的開端。宋代自立國以來,就一直在外族的交相入侵下求生存;政府無法有效解決外族寇邊問題,只得以繳納大量歲貢來換取和平。此種苟且的態度,使得宋代被後人冠上「積弱不振」一詞。即便如此,卻仍然無法掩蓋宋代中國文化高度發展所綻放出來的燦爛光芒。
中唐安史之亂後,由於北方接連不斷的戰火,迫使原居住在北方的居民大量南遷,為當時仍地廣人稀的南方帶來開發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爾後經歷五代十國,至宋代時,南方已取代北方,成為中國人口集中、文化發展的中心。唐代時,因為城市貿易有地點、時間上的限制,使得商業發展受到侷限;但這種限制至宋代時已經消失,商人可以自由地在城市中進行交易,且更進一步地將貿易擴展到城市之外,使宋代城市規模漸超越以往,各地市鎮也逐漸發展。隋唐時所開著的大運河此時仍繼續發揮功用,便利南北貨物往來,增加了貨物的流通性。宋代商業貿易的發達,增加了社會上的小康之家。富裕的社會風氣,成為發展文化的一個重要條件。
科舉制度至宋代時成為政府揀選政府官員的一個重要途徑。唐代政治為貴族政治,政治權利為世家大族所把持;但在經歷唐末、五代十國的戰亂後,這些世家貴冑逐漸沒落,權力不勝以往。在宋代繼唐代世家大族而起的是另一批由科舉制度造就出來的士大夫階級。五代時,由於武人干政,造成政治不穩、政權更迭頻繁;為了避免此一弊病,宋代自立國之初,便以「強幹弱枝」為國策,其中一措施便是推行「文人政治」,提升文人的政治地位;並以科舉制度作為遴選政府官員的主要途徑,使地方人才有機會進入中央,為政府效力。這些由科舉出身的士大夫,構成了宋代主要的統治階級。
而發展科舉制度意義的另一個層面,是此制度並不允許任何人永遠掌握政治權利,避免危害君權的可能。之前曾經提過,宋代商業的發達,增加了社會上的財富。一般平民百姓在經商致富後,便有能力栽培後代,鼓勵子弟讀書,以考取功名,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而印刷術至宋代又有新的發展,大大地降低了書籍印製費用,普遍了知識在社會上的流通性。這些社會發展,加上科舉錄取後可獲得的優渥籌賞,使社會中讀書人口大大增加,提升了宋代社會文化水平。雖然宋代大量開放科舉錄取名額,提供尋常百姓晉升之途;但報考人數大量增加也使科考競爭也比前代更為激烈,使人不禁質疑科舉制度究竟能促進多少的社會流動(且已掌握政治權力的高官貴冑子弟較一般人家擁有更多資源;又有門蔭的不成文規定,人為地破壞了科舉制度的應有的公平性)。但即便如此,科舉制度仍提供更多步入仕途的機會;且更重要的,是增加宋代社會的普遍知識水準,這是使宋代之所以能發展出超越前代的文化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科舉制度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使儒學地位在宋代知識界又得到提升。中唐安史之亂肇因於中國境內胡族叛亂,此一亂事不但開啟了中國北方的連綿戰禍,也改變了過去中國「華夷一家」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漸趨嚴格的夷夏之防,這表現在學術上是學者如韓愈、李翱之輩開始提倡中國儒學的復興,摒棄外來文化,致力於中國本位文化的建立。這種趨勢延續至宋代而不斷,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宋朝自立國以來,便在外敵環伺下求生。為了換取和平,宋朝政府每年必須繳納大量歲貢,但仍然無法完全使國家免於外族侵略的威脅。國家處境的艱難激起了士人的民族意識。而宋代政府以文治建國,科舉制度「一舉成名天下知」加上其他隨之而來的附加價值,使得民間仕子紛紛趨之若鶩。科考以儒家典籍為考試科目,等於是間接地鼓勵士人研究儒家學說,儒家地位在宋代時又得到提升。儒家思想、科舉制度、加上民族意識的發展,是使中國本位文化得以建立的原因。科舉制度使儒家傳統在宋代又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儒者向來提倡的「尊王攘夷」思想和民族意識又互為作用,「造成士大夫的自尊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竭誠崇拜和擁護,因此自然卑視外來文化。加以契丹、女真等外族的侵凌,遂使宋人對異族於卑視之外,益以仇視」 。
以上都是宋代之所以能夠發展出超越前代文化成就的重要原因。外敵環伺,使宋代政府沒有機會投注太多心力於邊疆事業的經營,但卻給了國家內部文化充分發展的空間。科舉制度以及儒學在宋代重新地得到重視豐富了宋代知識界,因此有「理學」的發展;也使宋代一般社會風氣較以往各代嚴謹。驚人的商業成就則為一般社會文化發展帶來更多潛力。有典雅的詩詞和充滿意境的文人繪畫以配合士大夫的高尚口味;而一般市井小民在有錢有閒之後,也開始發展屬於自己的休閒生活,因此有較為通俗的曲和話本小說來因應他們的需求。以上種種在宋代中國才出現的社會現象,是否能讓一個人暫且放棄以「攻城掠地,開疆擴土,萬族歸順」的帝國主義式強權標準來評量一個國家的強弱,轉而注意宋代在文化方面所綻放出來的異彩,而對這個「積弱」的朝代另眼相看?
約與中國宋代同一個時期,西方歐洲也進入了著名的文藝復興時代。商業經濟復甦,城市在各大交通要道上興起;各種人文思潮也蠢蠢欲動,西方的人們厭倦了一切都以宗教為中心的生活,要求重回古希臘羅馬以人為本位的時代,因此有所謂的人文主義興起,文學、音樂、建築、繪畫等各項藝術無不綻放出強烈生命力,將這個時代妝點得多采多姿。以「文藝復興」為起點,爾後的西方經歷了各式各樣的變動,如民族國家的興起、宗教革命、海權時代的開展,才有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出現。敘述至此,不禁讓人心裡浮現一個問題:既然中國在宋代的發展和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所出現的變化有如此多的相同點,那為何兩個地區後來會走上了兩條如此不同的道路?
針對這個問題,西方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提出極富思考性的見解。在其名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韋伯認為喀爾文新教的禁欲主義和預選說是激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動力;而在之後的《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中,他又試圖解釋為何中國無法發展出資本主義。因此在這裡,我們也先借用韋伯的觀點,試圖解釋為何資本主義在中國無法生根茁壯。韋伯認為,結構上的障礙與儒家(韋伯稱之為「儒教」,但為了配合前面敘述,改用「儒家」一詞代替)思想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在結構障礙方面,韋伯認為中國的國家政府結構和社區結構是限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有民族國家的興起 — 國家的權力擴張,更深入人民生活,單一司法體制被建立,國家組織也逐漸有科層化的趨勢 — 這些都是促使後來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條件。然而在中國,這種情況是相反的。自宋代後,中國人口急遽增加,經濟型態也日漸複雜,但是國家政治機器(指政府的機關如法院、議會或國會以及公務人員) 卻無法配合國家實際發展,而有所改變。「天高皇帝遠」是古代中國政府和人民關係的最佳寫照—政府無法進一步地將其觸角深入一般人民生活,也未能擴大地方行政中心的控制力,因此和人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傳統上是以家族為基本構成單位,嚴謹的親屬關係構成了堅固的傳統主義堡壘。人們的認同對象是其所屬家族,而非國家,人們仍然停留在效忠家族的階段。以上兩種情況都是使中央政府無法有效控制地方、或是將其整合成一整體的重要原因。此外,中國也未能發展出一個具理性、正式化的司法體系,而這也是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司法執行掌握在個人私欲、特權手上,不確定性太高,無法有效保障商業投資。韋伯認為,這也是限制中國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個原因是儒家(儒教)思想。韋伯認為儒家思想只使人們接受事物的既存狀態,而不會在社會中引發促進改革、變遷的力量。過度強調個人內在德行修養,而非鼓勵人們關注外在事物,儒家學說高度的「世俗化」傾向使人們反而容易適應、習慣世俗傳統,而非進行任何創新改變。當我們發現北宋仍有范仲淹、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而在理學盛行的南宋此類救亡圖存的行動卻付之闕如,我們就可以更瞭解韋伯所指為何了。此外,科舉制度以儒家經典、詩詞創作為考試科目,使仕子紛紛專注於「雋詠的詩文、詞韻和古典義理的引喻舉證之上」 。在儒家所認可的標準中,德行修養、文學造詣才是評量是否足以勝任政府公職的標準,而非專業的技術知識。在這種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士大夫,自然不會關心經濟狀態的發展,也不會致力於己身專業化技術的養成,而這些卻都是發展資本主義體系的有利因素。基於上述的兩個理由,儒家在韋伯心目中,成為「一個無情殘酷地追求聖典、聖人之傳統」 。
總結上述觀點,當西方歐洲諸國在文藝復興後經歷民族國家的建立(同質性提升)、科層體制的發展、國家權力的上升、思想體系的突破等變動,而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宋代之後的中國卻因為在政治、思想等層面的發展受到限制,而無法產生繼續的突破,一直要等到清朝末期,才有另一次較為醒目的發展。
然而,這種以西方文明發展為中心來比較其他文明的發展的作法是否有其合理性存在?不僅是韋伯,近來也有許多西方學者習慣以西方歐洲文明的發展歷程為標準,來討論為何其他地區沒有出現類似西方的發展。這種研究態度的好處是跨文化的比較為我們在瞭解歷史的發展時,提供了另一個向度的觀察點,讓我們得以全新地思考中國文明的演變;但缺點卻在於此種觀察角度極容易產生「文化霸權」、「文化優越」的流弊。以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為正軌,即暗示其他發展模式都不符合標準,都是不良的,進而否定了其他文明存在、發展的價值。然而,歷史的發展並沒有任何固定的「標準」,每個地區都各有其獨特的演進模式,也都有其存在價值,這不是單純的西方白人文化優越就可以推翻掉的。因此,借用西方學者的觀點來理解中國歷史時,固然給我們研究歷史的另一種啟發;但我們必須注意自己論述的態度和方法,以免落入「西方白人資本主義優越」的窠臼。
~ 參 考 書 目 ~
1. 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1996。
2. 賈志揚,《宋代科舉》。台北:東大,1995。
3. 陶晉生,《中國近古史》。台北:東華,1995。
4.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收入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中國通史教學研討會編,《中國通史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1。
5.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編論著選譯》,第一冊《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
6. George Ritzer著,馬康莊、陳信木譯,《社會學理論》上冊。台北:巨流,1998。
7. Anthony Giddens著,張家明等譯,《社會學》上冊。台北:唐山,1997。
8. Robert P. Hymes, “Song China, 960-1279,” in Ainslie T. Embree and Carol Gluck, eds. Asia in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 A Guild for Teaching (Armonk: M. E. Sharpe, 1997).
最後由 小地震 於 2004-05-25, 00:18 編輯,總共編輯了 1 次。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二] 宋初政治
[b][size=150][color=blue]宋初政治[/color][/size][/b]
西元960年、陳橋驛一地兵變發生不久後的一個晚上,在開封新宋王朝偌大的寑宮中,一個人兀自地從睡夢中驚醒,他就是這個新王朝的建立者—趙匡胤,而這已經不知道是他在藉政變奪取帝位後第幾次地被惡夢驚醒了。一次又一次地夢見「陳橋兵變」的故事重演,但是這次,他的角色並不是那個因此鹹魚翻身的政權新貴,而是一個從高位上被踢下來的落敗老狗。且困擾著趙匡胤的還不只這些,除了潛在的政變危機,還有北方遼國的威脅(燕雲十六州的失地總是讓他耿耿於懷)。到底要怎樣才能讓舊事不再重演?到底要怎樣他才能不重蹈前面幾個王朝君主的覆轍,而使自己的國祚永存?這個問題在趙匡胤的腦海中一直不去。突然,一個想法浮現在他的腦中,這是他長久以來失眠所換來的寶貴代價,而且他知道這也將是他最後一個的「難以入眠」了……。
如同上面所敘述的,北方和遼國之間的國防問題和內部可能會出現的權力傾扎,是威脅宋代生存的兩大問題。因此,宋太祖在即位後,便思量如何解決,以保國祚永存。在他仔細權衡內外局勢後,他決定採取「先安內後攘外」的步驟,先致力於國家內部的建設,消除潛在的反對勢力,再考慮如何對外。而在這樣的考量下,宋代在太祖的領導下,發展出所謂的「強幹弱枝」政策,而此政策也在後來演變成為宋的基本國策。
「強幹」,指的是鞏固中央;「弱枝」,則是削弱地方的權力,大致可分兩個向度:「中央集權」以及「文人政治」。
在中央集權方面,太祖首先以整頓禁軍為務,排除軍中異己將領,演出「杯酒釋兵權」,勸退有實力將領,整飭禁軍,使之成為護衛中央的軍伍,而非野心家用以叛亂的資本。再來是削弱藩鎮勢力,使節度使脫離原來地盤憑藉,以文人充任處理藩鎮軍務的文官,調派政府中央官員至地方監督地方稅收及政事;並在有地方節度使出缺時,以文人遞補。太祖並以樞密院掌軍事,由皇帝直接指揮;有事樞密院派軍官統領軍隊出征,避免領兵之間過度熟悉,而有兵變可能。於是地方各項大權,便逐漸歸於中央。
在「文人政治」方面,為改善五代君權低落、士風頹靡的弊病,太祖試圖藉「儒家的道理來重新樹立綱紀,改變政風」1:表揚忠義之臣,樹立不殺大臣、言官的家法;提倡文治,優禮文人,壓抑武臣;並重開科考制度,增加錄取員額,使之成為政府選取官員的主要途徑。而在政府的特意提倡下,宋代文風漸盛。
而在對外經略方面,太祖因顧慮國家資本尚未強至可和北遼一決雌雄,因此將經營重點首先放在江南諸國的經營。在西元963至975年間,太祖先後滅荊南、南漢、南唐。至西元976年太祖駕崩後,由即位的的太宗光義完成其未成之志業。
978年,太宗克降北漢,於是整個中國地區,就只剩宋遼兩大強權了。在太祖時代,因為國力尚未成熟,因此並無經略北方的計畫。西元974年,在宋遼地方長官的促成下,宋遼開始了雙方的建交關係,皆有互派使臣問候彼此的紀錄。但在979年時,這種和平關係因為太宗企圖趁降服北漢之機、收復燕雲十六州而告結束。這場戰爭是以宋敗作為結束,而後直至真宗澶淵之盟建立前,共有二十五年的時間兩國不互通使臣。
宋所面對的北遼和之前中國王朝所面對的外族是不一樣的。早在宋建立之前,遼即開始了民族的漢化,在維護契丹人原來習俗的情況下,起用漢臣制訂典章制度,採取不少漢人的典禮儀制。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遼國並不能單純以「蠻夷敵戎」視之,她也具有強大的文化發展潛力;且更重要的,是凌駕宋的武力。遼在建國後,也不斷去提升其國際地位。然而,可惜的是,宋朝並沒有察覺到這種狀況,(或者是說宋並不承認這種事實),還是以天朝的中國自居;即便太祖時期和遼建交,也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為緩時勢而已,並不把遼視為是對等的國家看待。如在〈小帝國的辭令:宋代與其鄰國的早期關係〉一文中,作者記錄西元978、979兩年時,宋政府稱遼「向宋朝贈送禮物稱為『獻』」,而稱宋代「向遼回贈的禮物稱為『賜』」2,明顯表露出宋代這種無視客觀現實,而仍採自尊自大的大中國心態。
澶淵之盟是宋遼關係的另一次轉折。西元1004年,遼聖宗南侵,真宗依寇準之意親征,兩軍在澶淵一地對峙。後來在宋降將王繼忠的調停下,於次年成立了具歷史意義的澶淵之盟。宋人以每人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為代價,換來了往後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或偷安)。
回顧宋初時以「強幹弱枝」為基本國策,固然成功地消除晚唐五代以來藩鎮割據的弊端,建立強大中央權威,但也於其中產生了不少弊病。陶晉生認為,由於政府只注重中央禁軍的訓練,忽略地方軍隊的培養,導致地方軍無用,無法抵禦外敵。且自太宗以來,宋政府便不斷擴充禁軍數目,卻無法提升素質,「軍隊的來源,絕大部分來自招募,其份子多半是無業遊民和負罪的亡命者,每遇荒年,朝廷更以招兵為救荒的手段」3,因此禁軍雖龐大,卻不能用。地方軍無用,中央禁軍素質又低落,自然無法抵禦外敵,也自然在對外經略時,必須以納歲貢來換取和平。
過度地提倡「文人政治」也造成國家問題。由於宋代開國君主竭力提倡文治,使社會上養成了普遍「重文輕武」的風氣。由於地位高,政府待遇又豐,「影響到第一等人才都不願做武官」4,國家因此也少了許多軍事人才。
平心而論,宋初以「強幹弱枝」為發展大要,實因為她面臨了晚唐五代時的武人驕縱弊病,為了鞏固國本,才不得不如此。但這種政策持續到後來,我們便逐漸發現它對宋代國家的不良影響:軍務廢弛,武備不修,使得國家無法對抗外侮;過份發展「文人政治」,大量增加取士名額,加上科舉取士產生的弊端,使政府冗員逐漸充斥,影響政府財政。國家經營至此地步,宋人該何去何從?所幸政府中仍有些許有志之士,願意為改革時弊而挺身而出,因此才有後來的慶曆、熙寧兩次變法。
~ 參 考 書 目 ~
1. 傅樂成,《中國通史》下冊。台北:大中國,1996。
2. 陶晉生,《中國近古史》。台北:東華,1995。
3.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第2-3章。台北:聯經,1995。
4. 鄧之誠,《中華兩千年史》,共五冊。第四冊,頁58-111。北京:中華書局。
5. 王膺武,〈小帝國的辭令:宋代與其鄰國的早期關係〉,收入其《歷史的功能》,頁140-172。香港:中華書局,1990。
6. Anthony Giddens著,張家明等譯,《社會學》上冊。台北:唐山,1997。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三] 兩次變法
[b][size=150][color=blue]兩次變法[/color] [/size][/b]
「慶曆政改」與「熙寧變法」是北宋中後期、政壇上出現的兩次革新圖強運動,前者發端於仁宗慶曆三、四年(西元1043、44年),是范仲淹等人主導下所出現的漸進改革;後者則是於前者改革失敗二十餘年後,由王安石一輩所發起的救亡圖存運動,這一次的改革開始於1069年、宋神宗在位期間,而隨北宋覆亡於金女真告終。
兩次的變法,首先反映出來的是「北宋開國以來的政治措施,逐漸發生問題」1,若不進行改革,國事則無以為繼。其次,兩次圖強運動都是在有志士大夫的領導下開始,表現出「北宋初年儒學復興,儒生逐漸成為政治和社會的中堅」2;深受儒家典籍教育的影響,這些士大夫的榮譽感既強,經世濟國之責任感也重,使他們願意在國家有難時,不顧個人切身利害,挺身而出,為國家存亡盡一己之力。
然而,極為不幸的是,從歷史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這兩次的變法都以失敗告終,再多的努力也無法阻止北宋步向衰亡;甚至改革所生影響,也餘波猶存,影響南宋偏安初期的政局。寫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北宋兩次政改為何都宣告失敗?有志士人提倡圖強,希冀以一己之力改變國家命運,卻為何最終仍只能高嘆「孤臣無力可回天」?究竟在政改進行時,北宋政壇上又有什麼樣的因素左右時局,操縱著變革的成敗?
在中國傳統的君主政體下,主政者(宰相)若想要使改革計畫能成功推行,在其計畫過程中必須先考慮下列兩大變項。首先,他和權力來源中心(皇帝)兩者間必須先有良好的默契關係存在,才有將其理想付諸實現的可能。其次,主政者也必須要能事先考慮在保守/反對勢力中間可能會出現的反彈—一革新政策在實踐的過程中,必定會危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之反對大刀闊斧式的改革,這些人姑且稱之為「保守份子」;然而也有些人純粹是由新政策可能會引發的問題的角度出發,質疑新法的可行性,這些人即是所謂的「反對勢力」。主政者必須先能計算出由這些保守/反對者構成的反動力量,對新法的推行會造成多大的阻礙,才能減少政改過程中可能會產生的變數。而在這兩大變項中間,所存在的另一個決定性要素是主政者居間協商的行政能力。若主政者協調能力佳,不僅能化干戈為玉帛,更能和平地消減原來的反對勢力,以期加入革新政策的行列,為塑造國家共同遠景而一起努力。
宋代為推行文人政治,其中一項措施就是重開唐代就已出現的科舉制度,以其作為選任政府官員的方法。科考制度作為一個尋常百姓得以進入政府任公職的主要、且是唯一的途徑,以儒家經典為考試科目,逐漸培養出一批非官宦之家出身的士大夫。其中某些人(占少數)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一生忠君為國;在國家遭遇危難時,他們通常是首當其衝,率先出來改革的一群人。如劉子健所說,他們「通常都處於力求改革國政的政治地位上」3。
北宋中葉,國家逐漸浮現危殆之象。宋代歷次對外戰爭,多以失敗告終,因此政府不得不對外繳納鉅額歲幣,以換取短暫和平。歲幣連同抵禦外敵而年年增加的軍費,以及運作龐大官僚體系所需的俸祿,為北宋政府國家財政支出帶來極大負擔。社會上,土地兼併問題嚴重,擁有土地者多為不必納賦稅的特權階級;國家沈重賦稅壓力落在一般平常百姓頭上,再加上繁雜的差役,使得人民莫不怨聲載道,民力疲乏。國事進行至此,已面臨救危圖存之秋。因此,這批深受儒家理想薰陶、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士大夫就挺身而出,領導國家的改革。「慶曆政改」、「熙寧變法」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所出現的兩次變法改革。
「慶曆政改」(西元1043至44年)是由范仲淹、韓琦等人所領導的政治變革。改革發生時,北宋內部除了有上述各項問題,在外交上,也同時面臨遼(遣使索地)和西夏(寇邊)雙方面的侵擾。范、韓二人當時因為鎮守陝西有功,加上宋內地也發生王倫兵亂,需要有治兵經驗的人來掌控大局,因此兩人先後奉召回京,分任參知政事、樞密使(43年8月)。而後,范、韓二人上「十事疏」4(43年9月),提出十項富國強兵計畫,作為此次政改的綱領。然而改革進行未至一年,改革一派便陸續離去,再過不久,所行新政也隨領導者的離開而宣告廢去。
慶曆政改為何失敗?首先是因為外敵威脅的消失。陶晉生認為,慶曆改革的發生,有一部份原因是為了外患,「外患一旦消失,對於改革的需求,就不如慶曆初年那樣迫切」5。1042年,遼遣使索地一事以宋增歲貢二十萬告結;1043年,西夏元昊也因國力困頓、貪戀宋的歲賜,而願意向宋稱臣。「危機解除後,當政者又恢復了保守的政風」6。其次是因為仁宗對改革一派的不信任,而這和反改革一派對新政人士的污衊攻奸有關。新政一起,許多人的未來隨即受到威脅,如隨「抑僥倖」而頒佈的「詔減蔭補『任子之恩殺』」、「詔減『奏薦恩澤』」政令即有損到許多顯貴達觀子弟的利害。這些既得利益者為了鞏固自身權益,便在政壇上和改革派展開了一場明爭暗鬥。1044年夏天,仁宗耳聞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結為朋黨,即便歐陽修進奏「朋黨論」,卻仍然無法斷絕仁宗心中疑慮;同年秋天,夏涑令人「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7,陰謀誣陷富弼有造反之意。改革派之所以能夠意氣風發地推行其改革計畫,其權力來自於在位君主的賜與;也就是說若未得到皇帝首肯,儘管改革派的理想再高,也無濟於事。君主之所以任用士大夫,原因在於他需要一批人才來協助他推動這一部巨大的政治機器;但「絕非分享他的終極權力」8。但是有志於變革的士大夫其若未謹守其政治主張,很容易被「誤導成為對君主的終極權力的一大威脅」9。反對改革者發現了君主‧改革派之間這層微妙關係,並善加利用,僅用一些耳語、謠言就鬆動了兩者間的互信關係。1145年,主持新政的范、富、韓等人相繼罷去,短暫的慶曆改革就此劃下句點。
之前曾經提過,改革若要成功,前提是主政者和權力來源之間必須要有極佳的默契;主政者要能洞察機先、預先發現可能有的阻礙;以及居中協調能力。可是在這次的慶曆改革派中,我們卻無法發現這三要素。反對改革一派只消在仁宗面前道長論短幾句,君主和改革派之間的信任就不負存,顯見兩者未能消除其中矛盾。新政一舉推行,原本就會干犯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忌諱。然而,改革派未能預見此可能有之阻礙,並試圖化解其中張力,如將新政次第推行的同時,也留足夠後路給保守份子走,因此引起許多反對聲浪是可以預見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發現改革派一些行事為人上的缺失,如范仲淹據聞「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富、范、歐陽、尹常欲分君子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10;且改革派往往習樹立政敵,凡「不附己者,力加排斥」11,這種對「支持‧反對」兩者清楚的二分法,不留任何餘地于人,常使事情演變得毫無轉寰餘地,只徒增仇敵,莫怪乎此次政改會失敗。
同樣的情況,仍然可以在二十餘年後的「熙寧變法」中發現。不同的是,此次變法所掀起的狂風巨浪更進一步地將北宋推向覆亡。
慶曆政改草草結束,北宋內部問題並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縱然仁宗、英宗都不失為賢君,但因理財無力,又無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乃至『雖儉約而民不富,雖優勤而國不強』」12,國勢日益惡化。治平四年(西元1067年),英宗卒,神宗繼之即位,乃力圖振作,因此便重用當時著名於外的王安石,進行變法。
和前次「漸進」、「緩和」的慶曆政改相比,王安石此次提出的圖強計畫是一次「大規模的根本性變法」13,所涵蓋、影響的範圍更廣,也涉及到更多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要想完成此次改革,王安石所領導的改革派所要冒的風險相對地也比之前要高上許多。
在這裡,筆者並不打算一一詳述王安石的改革內容,而是想瞭解是什麼因素在左右此次改革的成敗。雖然從現代看過去的後見之明,我們知道熙寧變法仍以失敗告終,但是否在改革未行之前,就可窺見失敗的端倪?一次神宗和韓琦討論在其去後、有誰可繼之為相的問題時,韓琦知道神宗屬意人選為王安石後,馬上答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呂誨則認為「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以上兩段話皆出自《宋史》,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訊息:(1)在朝名士多不認為王安石足以勝任相職;原因在於(2)王為人執拗,過份固執,沒有接納他人意見的雅量;且用人常只重才能而忽略德行的重要,使「會玩弄手腕的官僚,整天包圍住王安石,故意和他討論正式經義,使旁人無從接近,藉此蒙蔽他」14。陶晉生曾強調若以《宋史》記載作為王安石生平研究的資料,必須先進行史料的鑑別工作15,因為他認為《宋史》中關於王安石的史料多自變法當時屬於保守派的司馬光的《涑水記聞》以及邵伯溫的《邵氏聞件前錄》等著作中關於王安石的紀錄而來,對王安石的評價可能會因政治立場上的不同而多給予負面批評。即便如此,我們仍可推知王安石的個性:常只見理想所建構出的願景,而忽略現實環境的限制;過份堅持己見,無法容納不同聲音;也無法協調不同意見,因而增加了衝突發生的可能。朝臣深知王安石此種性格,預知其上台後,「天下必困擾」16。因此王在未為神宗所重用前,「已中舉朝之忌,後來一切設施,不論是非,動遭抨擊,不與為伍」17。改革並非只是一、兩位朝臣的責任,其成敗有賴於在朝諸臣攜手並進,捐棄成見,才有開花結果的可能。然而,不幸的是,許多在朝中有影響力的大臣均拒絕與王安石合作;使變法在未開始前就已蒙上了一層陰影。
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策劃、指揮變法的機構,展開這次北宋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變法圖強。在1069至1076年的八年間,新法於王安石主持下,漸次推行18。為了便利新法的實施,王安石大量引進新人,如呂惠卿、章惇、曾布、呂嘉問等,作為新法實施的後援。然而這些政治新進,雖富有學識才智,但宦海歷練未深,操守氣度均嫌不足,如呂惠卿的行事作風便反覆無常,曾布也曾竭力排斥異己者。這些政治新貴雖然對王安石新政的擬定、執行貢獻極大,但卻無王安石經世治國理想,為新政的前途,投下許多不確定的變數。
和熙寧變法相比,屬於漸進改革的慶曆政改尚且引起如此多的反對聲浪,更何況王安石的新政是以大規模改變宋廷立國制度為目標。因此,新法頒佈後的不久,反對者也開始攻擊王安石的施政措施。在這些反對聲音中,有因新政干犯到自己利益而大加阻擾者19;也有因認為新法擾民而不與支持者20。儘管這些批評多流於意氣之見,但其中也不乏切重實際的言談,且新法實行的確有不妥之處。舉「青苗法」為例,規定由政府借錢予民,以避免農民在青黃不接、急需用錢之際,為富豪剝削。新法立意雖佳,但真正實行時卻出現許多不妥之處,一方面是法制設計不良,未有周全配套措施;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有不肖官吏藉新法營私。如便有人指出「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一旦飢荒來臨,人民便無以為繼,仍不免受積蓄之家剝削;也有朝臣認為「愚民知舉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沒有足夠利用貸款的知識;加上有官吏以「多借出為功」21,強迫人民借貸,未為人民帶來便利,反而徒增人民困擾。尤其是後者,更使反對者振振有詞。
政治意見上的不同在所難免,即便是同一黨派的人也多少會有想法上的差異。然而,若主政者能使眾人捐棄成見,顧全大局,即便是對立的雙方,也未嘗不無合作的可能。之前曾經提過,王安石個性偏執,「狷狹少容」,駁斥反對論點,儘管其中也有可取之處;且和自己意見相左者,均被他「目為不讀書的俗流」,富弼、韓琦、文彥博、歐陽修等人,紛紛被貶,司馬光也自行求去。王安石如此不容人的態度,完全否定協調合作的可能,也使這些反對者記怨在心,雙方未來的衝突遂不可免。
熙寧七年,適逢久旱,有地方官上陳「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連神宗見人民顛沛流離,也「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此時又有商人向神宗抗議市易務自為兼併,促使神宗下令調查。原本王安石聲稱絕不害民,但負責調查的曾布卻報告「市易務判官呂嘉問經營過當,謀利過甚」22,遂使神宗下令罷免王安石。臨去前,王安石薦以呂惠卿代己職,因此王安石雖離開,新法仍繼續推行。
新法進行至此,已逐漸出現敗相。神宗、王安石兩人政治理念並不一致,「神宗以富國強兵為目的,期能…湔雪前恥,炫耀國威;王安石則以化民成俗的三代之治為鵠的,富強不過是達到目標的手段」23。王安石雖遇困挫,但仍能堅持其政策;但神宗卻可因反對者太多、代價太高而選擇放棄。王安石此時的下台,表示神宗開始認為改革並不以用王政策為唯一,即便新政於王下台後仍繼續,但其意義已和開始有所不同。此外,曾布為王安石所提攜,卻攻擊其施政;呂惠卿繼王主政後,先外貶曾布、呂嘉問,後與王安國(安石弟)交惡,惡意陷害他,連王安石也成為其構陷對象,新黨一派遂陷入勾心鬥角的政治遊戲中。
元豐八年(西元1085年),神宗死,哲宗繼之即位,因年幼(十歲)而由太皇太后高氏(英宗后)聽政,以司馬光為相,舊黨得勢,不但盡廢熙寧、元豐年間所行新法,也貶逐新黨份子。但舊黨人也並非全然團結,如蘇軾、范純仁(范仲淹子)便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的舉動。但勸諫仍無濟於事;舊黨也分為洛、蜀、朔三派24,因政見不同而爭執時起。
哲宗以後,新舊兩黨何者得勢,全由在位君主執政意向決定。新黨得勢,必全力打壓舊黨;舊黨掌權時,也必如此。交相傾軋,雙方衝突越演越烈,此時的爭執,已非以改革與否為重點,而流為純粹的意氣之爭了。變法無成,卻於朝廷掀起另一次政潮。身為社會中堅、肩負國家興亡重任的朝臣不去思考如何求國家進步,整日投注於於國事無益的政爭之中;君主又無法再帶領有志之士進行另一次改革,另起新局,政事遂日益敗壞。最後在1127年,由女真的入侵為北宋的統治劃下句點。
政治改革的成敗,涉及諸多因素,如政策制訂的優劣、實行官吏的素質、社會環境風俗、實際實行時的落差等。筆者以上述三變項作為論述焦點,並不是要去否定其他因素在政改中可能具有的作用力,而是試圖以這三個因素為焦點,論證北宋兩次政改失敗的原因。因為已暫且否定其他因素可能會有的影響力,是以在整個論證的過程中,難免會有錯漏之處,這尚待讀者予以指證。政治改革並非僅是紙上談兵,一政策在施行過程中可能的困難度以及任何無法預料的變數,也並非在這裡用三言兩語就可道盡。范仲淹以及王安石在北宋中後期主持的兩次變法圖強,其所面對的壓力與挑戰,都是處於現代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以此題作文,並非自大地想指出這兩位前人在政改執行過程中所犯的缺失;而是以一個後人的角度,觀察北宋中期後政壇上的盛衰起伏,且因感佩范、王等人於國事艱難之際,仍願意挺身而出,為國家興亡盡一己之力,而向其致敬。
~ 參 考 書 目 ~
1.傅樂成,《中國通史》下冊(台北:大中國圖書,1996),第二十、二十二章。
2.陶晉生,《中國近古史》(台北:聯經,1985),頁33-42,85-95。
3.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冊四,頁113-154。
4.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香港:新亞研究所,1973),下編,〈歐陽修與北宋中期官僚政治的糾紛〉,頁129-255。
5.劉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劉紉尼譯,收入《中國思想與制度史論集》(台北:聯經,1976),頁123-162。
6.劉子健,〈梅堯臣《碧雲騢》與慶曆政爭中的士風〉,收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1997),頁102-116。
7.劉子健,〈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收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1997),頁117-142。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四] 靖康之難與南宋政治
[b][size=150][color=blue]靖康之難與南宋政治[/color] [/size][/b]
若要以一段話簡論北宋徽宗的統治,韓非子人主篇中的「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也…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無疑是此一時期政治概況的最佳寫照。徽宗是歷代中國君主中,少數以藝術長才聞名於後世的皇帝;但他本人並不熱衷於政治經營,也無心過問政事,遂給了有心人可趁之機,一方面藉投君主之所好而獲重用;另一方面因君主對政事的疏忽而得以把持朝政。蔡京和童貫就是此時扮演小人奸臣角色的重要人物。
西元1100年徽宗即位後,為了平息長久以來僵持不下的新舊黨人之爭,便以調停兩黨歧見為務,同時以舊黨韓忠彥(韓琦子)、新黨曾布為相。然而韓曾兩人不合,無法合作,鷸蚌相爭,卻是為蔡京帶來了可趁之機。先是蔡京利用宦官童貫為其在徽宗面前美言;而後韓忠彥為了制衡曾布勢力發展,以「新黨人攻新黨人」為計,也主張招蔡回朝,使蔡京再度得以進入權力中心。蔡京雖然同屬新黨人,但對王安石變法政策,並沒有深刻理解的誠意。他在參與政事後的不久,便將韓曾二人一同排去,以朋黨、言官打擊政敵,獨攬大權。而童貫因助蔡京有功,掌握兵權。根據宋史記載,蔡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利用宋代累朝積蓄下來的財富滿足徽宗個人喜好,「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使「累朝所儲掃地矣」;而後又因徽宗好花石,強要民間進奉,以滿足徽宗個人慾望。蔡京在其十數年的政治生涯中,有三次先後罷相的紀錄,但之後均能重獲重用,或許就是因為他極能掌握皇帝的心思意念,也可見徽宗對他仰賴極深。然而,政治畢竟不只是兒戲,特別是中國傳統君主政體之下,天下百姓的福祉常常就操控在皇帝個人的一舉一動上。徽宗即位後並沒有體認到一個君主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身為人臣的蔡京也不知輔佐人君,助其擔負起治理國家的重責大任,使北宋就在這樣君臣的帶領下,慢慢走向衰亡。
這反映出中國君主統治傳統的一大弊病。綜觀歷代開國君主,他們之所以能夠在亂世蜂擁而起角逐的群雄中脫穎而出,其中一部份固然是因為天運所使然,但是最主要憑藉的還是自己的過人智識,以及卓越的領導才能。但是後來的繼位者不一定都具有先祖開宗立代的壯志豪情,對政治經營也不一定都有興趣,使個人因素佔主要成分的君主政治品質不免因此大受影響;若在下臣子又不能克盡輔助之能,反而利用君主政治的弱點來為自己謀利,那政治局勢如何便可想而知。中國千萬百姓的命運被制度交付在這些統治者身上,只能被動地向上天祈求能賜下一個賢君;但不幸的是,中國「十個皇帝九個昏」,中國古代人民的生活情景可想而知。
收復失喪於遼的燕雲十六州一直都是深藏在宋代各朝君主心中的宿願,只是因為苦於遼的強大而不得實現。但是遼金之間的衝突卻讓北宋君臣看到了這麼一點的可能,想利用新興女真的強大以及遼的衰弱來奪回燕雲失地。因此在徽宗、蔡京等人的認可下,北宋遂有聯金滅遼的計畫(西元1111年),然而確實協定的成立,一直要等到遼金和談失敗以及金已經出師破遼後才告成形(西元1120年)。然而北宋當時衰弱的軍力,並不足以勝任此項工作,宋軍兩度進攻燕京都宣告失敗,而由金人獨力完成滅遼計畫,最後只得以輸遼歲幣、燕京代稅錢來換回不包括平、灤、營三州在內的燕雲失地。
宋金滅遼一役宋軍在軍事上的潰敗,使金人發現宋廷在國勢上的衰弱,遂對北宋生起輕視之意。1123年宋金簽訂的盟約中,曾經範定彼此「不得容納叛亡」;然而宋卻自己打破了這項約定,接納遼平州守將張覺,給了金人入侵的藉口。1125年,金人開始侵宋的軍事行動,以極快的速度直攻汴京。欽宗只得與金兵立訂城下之盟,才得以一時倖免。然而在金軍退去後,宋廷又恢復顢頇的態度,在和戰之間舉棋不定:既已決定與金和談,卻又在民意的壓迫下推翻和約,勾結遼人反金。於是1126年8月金人又再度南侵,11月時汴京陷落,徽、欽二帝、后妃、宮女、太監、官員遭俘,城中財物也被洗劫一空;27年4月金人劫徽、欽二帝連同宋宮室以及所掠得的財府積蓄、皇宮文物等離去北返,史稱「靖康之難」。至此,歷史上的北宋宣告結束。
「靖康之難」是中國史上的一個悲劇,卻也給統治者一個很好的教訓。國家軍政不修,養兵眾多,卻無法捍衛國土;君臣也無法誠實的面對時勢,間負起自己身為國家統治者應當負起的責任;再加上失敗的外交政策,終於為國家帶來國亡種滅的厄運。觀察宋遼關係。北宋自真宗澶淵之盟和遼維持盟約關係近百餘年,卻在遼衰弱時和金聯合滅遼,由此可看出宋人仍無法擺脫大中國的優越思想,一貫地習以夷狄的角度看待外族,盟約只是宋人維持和平的手段;如有機會,仍要伺機報復。另一方面,中國一向喜歡以「仁義之邦」自稱,但從宋遼之間的關係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宋廷為了取回本來就不屬於自己的燕雲失地,不但沒在盟友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反而是連同敵人踢她一腳,令人不禁感嘆現實政治中的額虞我詐,即便是自稱禮儀之邦的中國,似乎也不得不屈服於政治世界中的現實;也或許在現實中講求仁義禮智根本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
至於宋金關係,宋廷似乎沒有察覺到這個北方的新興民族的潛在威脅,並未對國際現勢中的「敵優我劣」的局勢有深刻的體認。遼一旦滅亡,宋金兩國立即陷入直接對峙的局面。宋即使藉金人之力成功奪回燕雲失地,卻未能為將來臨的挑戰做好準備,反而只是沈醉在收復失土「曠世」功績的美夢中。相較於宋,金人在與遼的作戰中成功地證明了自己的實力,也洞悉宋國不過是隻「紙老虎」,只不過在遼地上的統治尚未穩固前,實在不宜太快就發動對宋攻擊。但是什麼因素加速了金對宋的侵略?關鍵就在於宋接受張覺(降金遼降)的內附。以異族身份統治遼地對金人而言本就不是件易事,但張覺的背叛更使金感受威脅。若金人就此默許宋廷的背盟行為,一方面金的顏面無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金人無法穩固她在遼國上的統治,因為一旦開此先例,難不保將來還有其他遼降將會繼續背叛。因此為了杜絕後患,金人遂決定加速侵宋的計畫。1226年初金人與欽宗訂下盟約後,本來計畫在給宋一個教訓後就暫時打住。但沒想到的是宋廷對是和是戰舉棋不定,無力迎戰,卻又自行破壞與金和約,才又再度引來金兵,最後才有靖康之難悲劇的上演。由此觀之,外交政策上的失敗也可說是導致北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靖康之難後,康王趙構(徽宗第九子)隨即即位於南京,是為宋高宗。當時國內外的情勢,都極不穩定,外有北方金人亡國滅種仍揮之不去的陰影以及偽政權的威脅;內則有人民因戰亂流離失所,四處流竄,或結為盜賊,趁機到處劫掠。面對國家情勢的危亂,身為宋室留在中原的唯一子嗣,高宗必須好好思考要如何才能夠穩住所得不易的皇位,並在顛沛流離之中保持宋室的正祚。
金兵入侵後,各地都有由人民自行組成、為抵禦金兵、盜賊騷擾的民軍;且在大亂之後,分散各地的將領也開始重整散亂的部隊。這些武力本也可能會對高宗帶來威脅,但聰明的高宗號召勤王,對內高喊血恥復仇,激起民族精神聯合抗金,遂使這些武力轉為己用。面對內外均不安的情勢,高宗選擇以「安內攘外」作為策略,先同時以討伐/招撫的策略安定國內群盜,再想辦法對抗北方的威脅。最後在宋室君臣的齊心努力下,即便曾經因金兵追擊而四處逃亡,即便來自偽楚、偽齊的敵意不斷,即便中原、江南各地都曾經有盜賊為禍,宋室仍然能夠勉強應付,熬過最初幾年的艱難,在中國東南一隅取得偏安之勢。
在宋金作戰之初,高宗即不斷遣使至金,希望兩國可以休兵和好。但金一開始的政策是以消滅宋為主,因此對高宗的卑辭乞和並不容許。但至後來,宋廷實力在局勢稍微穩定後逐漸增強,金屢次命偽齊亡宋皆不可得,漸感到要徹底瓦解宋的統治並不是件那麼容易的事,遂同意宋金和談。
與金求和,是高宗心裡長久以來的宿願,家破人亡的悲劇固然使他心裡感到悲痛,但更令他更為恐懼的是與金的戰亂連綿,「經過在金兵營中做質押,從揚州倉皇逃過長江,從寧波逃到海上四十天等等的驚險」,種種的困挫使他極不願再繼續這場戰爭。且若宋朝在繼續對金的戰爭中僥倖獲勝,徽、欽二地一旦釋回,立刻會威脅到高宗好不容易才坐上去的皇位。是故高宗一向主張和談,只是在宋金戰爭最激烈時,為了避免打壓士氣,宋的遣使求和一直都是秘密進行的,對內並不公開。
但是和議一旦確定,金人派遣致宋商談和議計畫的使者到達宋國後,消息馬上在宋朝廷中傳開來,許多朝臣紛紛上言反對議和,使高宗感受到不少阻力。然而卻沒有人可以阻擋好不容易才談成的和議計畫,於是如何力排眾意,使和談得以完成,遂成為高宗在其統治初期所要面對的一大問題。
對外,與金和談考驗著高宗的外交手腕;對內,高宗也有相同困難的問題要解決:大將專兵,將領權重。原來宋廷在考慮到北方金人、和偽齊的威脅時,曾經在邊境地區先後設置了三十多個鎮撫使,作為南北兩大勢力之間的緩衝。而在面對內部的變亂時,因為高宗自己的武力不足,只得依賴地方將領之力平亂,並「不斷以高官厚祿、土地財貨來拉攏大將」,但卻「無法採取實際行動來強化中央權威」1。由於南宋局勢的穩定多有賴於地方將領的努力,遂使將領養成了驕恣縱橫的習性,常以其實力影響政府決策(岳飛曾向高宗提議立儲),直接干犯君主的絕對權威。此外,將領在弭平地方變亂時,常以安撫的策略將原來的盜寇納入麾下,收為己用,以壯大自己聲勢。但是這種性質組成的軍隊,其基礎「多繫於大將和部屬間的私人關係」2,諸兵「只知有大將,不知有天子」,軍隊儼然成為將領的私人武力,中央並無法有效控制。
宋太祖當初即是以兵變奪得天下,即位後為免舊事重演,便嚴禁武人干政,削弱地方兵權,確立宋代文人統治基礎,「強幹弱枝」因此成為宋遵行不悖的一貫國策。宋高宗即位後,也同樣遇到北宋初年太祖所面對的問題。高宗即位並非依循正統,很可能隨時都會有人起來挑戰他的統治權威;且大將專橫,武力又為將領所有,難保類似「陳橋兵變」的事情不會再度重演。建炎三年時的「苗劉兵變」使高宗深刻體驗到武將專橫對其統治力量的威脅。因此一方面基於祖宗家法,另一方面又考慮到自己的實際需要,高宗遂有收兵權的舉動出現。
「議和」、「收兵權」兩項任務是高宗為了穩固其統治地位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其中以「收兵權」為先。因為在與金和談的過程中,武將一直都反和最力;且也只有武將才真正擁有主導時勢的絕對力量,如韓世忠便曾經計畫挾持金使,破壞和議的進行。是以有這樣的先後順序。
從歷史的記載,我們知道這場政治鬥爭的結果是當時的相宰秦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以謀反之罪誣殺岳飛,用以殺雞儆猴,警告任何一個可能反對議和的文臣武將。之後,無人敢再對宋金和議發出任何議論;其他武將見岳飛為國效忠,卻落得如此命運,心中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油然而生,遂紛紛放棄手上兵權;其他仍未放棄手中大權的將領(如張俊)也於之後秦檜的整肅活動中,被排於外。至此,「求和」、「收兵權」兩項任務都宣告完成。
傳統上,秦檜因為賣國求和、構陷忠良而被後世人視為是千古罪人。但從之前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這兩項決策意見的來源是高宗本人,秦檜只是扮演好他政策執行者的角色;即便是殺岳飛的行動,若沒有高宗點頭,秦檜儘管權傾一時,也萬萬不敢殺害岳飛這樣一位重臣。因此若只將指責置於秦檜一人,未免有失公允,高宗也必須負起連帶責任。過去一般人在看這件史實時,往往放進太多道德批判,而忽略其中事實的分析。政治環境是現實的,而在傳統君主政體中,這個特質表現的更為明顯。文臣武將只是協助君主統治的「工具」而已,儘管一臣子為國家立下多少汗馬功勞,一旦他讓統治者感受到直接威脅,君主也會不顧過去情面,以除之為後快。南宋統治初年,將領專橫,明顯地侵害到高宗的統治權威,為了穩固其統治,高宗「不得不」限制將領兵權,只不過秦檜在採取較溫和的分化、眾建策略時,常被識破而宣告失敗,不得以才採用「殺人」這項較激烈的手段。岳飛之死,固然令人感到同情,但現實一點來說,也只能怪他鋒芒太露,義氣太盛,干犯太多禁忌,以致君主為自身安危而不得不痛下毒手。在中國政治史上,岳飛並不是第一個有功被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死於非命的武將。
至於秦檜,除了殺岳之外,似乎還有其他可以批判的理由。在除去武將之後,秦檜轉而用「朋黨」、「謗訕朝政」的罪名來打壓文臣,使南宋初年的政治仍無法抹去北宋末新舊黨爭的陰影。此外,為了消除不利於他(及高宗)的文字記錄、批評,秦檜藉著南宋建立之初圖書亡佚、急需重新徵集的事實,利用尋訪圖書的機會,挖掘不利於他的言論著作,甚至加以銷毀、禁止流通;興起文字獄,打壓異己。這樣禁錮言論、控制思想流通的結果,是使當時大難之後急需振作的士氣為之頓挫,有志之士不敢挺身而出,深怕重蹈岳飛、趙鼎等人的覆轍。南宋即便得以倖存,卻無法趁機力圖復興,再創新局;偏安三十一年,並沒有什麼太大作為,中斷了王室中興的大好時機。這是秦檜除了殺岳之外,真正要負的歷史責任。
~ 參 考 書 目 ~
1. 傅樂成,《中國通史》下冊(台北:大中國圖書,1996),第二十、二十一章。
2. 陶晉生,《中國近古史》(台北:聯經,1985),頁121-154。
3.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1995),頁203-215。
4. 劉子健,〈岳飛〉,收入其《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1997),頁185-207。
5. 遲景德,〈宋高宗與金講和始末〉,收入《宋史研究輯》十七輯,頁255-298。
6. 黃寬重,〈馬擴與兩宋之際的政局變動〉,收入其《宋史叢論》(台北:新文豐,1993),頁1-40。
7. 黃寬重,〈秦檜與文字獄〉,收入同上書,頁41-72。
8. 黃寬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收入其《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台北:新文豐,1990),頁105-139。
9. 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收入《宋史研究集》,第十九輯,頁203-256。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五] 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
[b][size=150][color=blue]新士大夫階層的形成[/color] [/size][/b]
唐代和宋代的統治階層在其組成本質上有極大的差異。唐代的統治階層可以說是魏晉南北朝世家大族傳統的一種殘留;而宋代統治階層卻是在中央政府努力推行科舉制度(以考試作為政府遴選官員的一種主要方法)下所產生的政治新貴。
歷經魏晉南北朝,世族始終存在。他們是社會上層的優秀份子,也是政治權力的把持者;其地位是在政府、社會大眾雙方面的承認下形成,即便是帝王之尊,也不能加以更改。然而,世家大族的地位在隋朝時卻開始面臨崩潰,這是因為此時廢除了世族用以維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的「九品中正制度」,而以「科考」作為政府取士的主要方法。然而,經歷幾百年時間的淬鍊,世族已建立起極為穩固的社會地位,重門第的觀念深入人心,非單單一個制度上的更改就可撼動。但改變依然在進行,新的社會制度正以一種極為緩慢的速度瓦解世族和一般社會之間的森嚴界線。
首先,「九品中正制度」的廢除使世族喪失了政治權力壟斷的特權,使他們無法再以地方為據點、建立起屬於自己家族的政治勢力。其次,「科舉制度」在隋唐兩代成為政府擢用社會人才的主要方法,一般平民百姓可藉應科舉任政府官職,提昇自己的政治社會地位;而原來的世家大族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地位,也必須使自己融入此制度,以求得生存。在〈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一文中,我們發現某些世族成員的確克服了這項困難,成功地適應了朝代更迭之際制度的變動,繼續維持自己的權力。然而,和以前不同的是,為了政治參與的方便,他們無法再佇留於原來的家鄉,政治權力在中央首都,偶爾他們也必須依政府的派令四處遷徙,因而喪失了他們和原來家鄉的聯繫。失去了土地的憑藉,世族成員對其家族光輝過去的認同逐漸演變成一種「心理」上的榮譽感,是成員對家族過去歷史的一種追想、一種記憶。但這種記憶、概念是很不可靠的,很容易因為人、事、物的演變而更動,甚至不復存在,(人都是健忘的,不是嗎?);所幸這些世族多有編訂「族譜」的傳統:清楚地記載家族世系變革,以區分「我群」、「他群」之間的分際。但到後來,這種傳統也逐漸被破壞。
真正轉變的關鍵是在中唐之後。首先,中唐之後,朝政為宦官所奪,他們是此時的政治權力中心,其他朝臣只能算是二流角色,世族政治地位不若以往。其次,安祿山的叛變以及接踵而來的藩鎮割據使中國北方陷入長期的混亂(直至西元九世紀中後宋朝的第二個皇帝趙光義統一中國後才得以結束)。在這兩百年的亂世中,世族的地位受到真正的打擊。戰亂所造成的顛沛流離,使家園殘破,許多人在戰爭中失去了原有的財富。之前說過,世族家族記憶的建立,有極大部分是仰賴族譜的修訂、紀錄;但修訂族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投注大量的人力、財力才得以進行。在這兩百年的亂世中,許多家族失去畢生累積下來的財富,許多檔案記錄也在戰火中被毀滅,在這種情況下,要繼續維持這樣一份家族記錄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此外,黃巢之亂後對世族的迫害也是導致世族傳統消失的一個關鍵因素,態度上的敵視或是以直接行動殘害,使家族輝煌的歷史頓時成為夢魘,使僅存的世族成員寧願選擇遺忘過去,隱藏自己的身份,以求得保全。就這樣,即便世家大族可以安然度過隋唐兩代的政權轉移,在唐代成功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地位、權力,卻無法在承受這一波時代洪流的衝擊,而逐漸消失於五代十國的社會中。在接下來的宋朝,代替世族而成為新社會統治階層的,是經由科舉制度的擢升而一躍成為社會中堅的士大夫階層。
每個政權在建立初始,都面對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如何穩定政權。宋朝在建立之初,當然也是如此,只不過她要面對的問題卻更為複雜:外有北方外族、地方割據政權虎視眈眈;內則要擔心自己藉以奪得政權的軍事叛變會否再度上演,也擔心這樣的統治是否能得到國內士人的認同。為了不讓五代時軍人專橫的問題再度發生,宋初統治者所計畫建立的是一個以「文治」為主的王朝。「科舉制度」是這個遠景建立的一個重要機制:大量增加錄取名額,使之成為中央政府選拔重要官員的主要方法;在皇帝首肯下開放政治權力的參與,而非由少數人壟斷。此政策巧妙的運用使宋朝將可能存在著的反對勢力化為對政府的忠心,建立起宋代文治的基礎。而科舉制度作為宋代立國的重要制度,也在此時逐漸發展,日益成熟,從北宋初發展出唐代所沒有的「彌封」、「謄錄」辦法以確立考試的公平性,到北宋中朝臣針對科舉制度存在的價值、考試的必修科目等議題開始的一連串討論以及相關改革措施,我們都可以發現這種趨勢。我們也可以發現「一舉成名天下知」所散發出的強大吸引力,對知識份子起著莫大作用,「科舉」自宋代起漸成為士人的一種生活方式,牽引著此後千千萬萬中國仕子的喜怒哀樂。
使宋代士大夫獲取統治權力的關鍵在於通過科舉制度,但和「九品中正制度」不同的是,科舉制度並不允許他們將其努力奮鬥來的權力地位直接傳給後代子孫,雖然高官子孫可藉由蔭任制度補官,但掌握權力的真正關鍵還是在於通過科舉考試。因此應試者及第後並不能就此高枕無憂,他們必須好好思考如何才能夠將自己積累的權力財富傳承給後代子孫,使家族枝葉綿延。而此時北宋中期范仲淹設置的「義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答:由家族中有成就者購置田產、興建屋舍,贍養家族親人,並集族人之力共同栽培族中有潛力的子弟,使之準備科舉,繼續挑起興盛家業的重責大任。因此北宋中葉後,各地紛紛出現了類似范氏義莊的組織。各地組織外型、架構、經營方式或多或少都會有些不同,但其本意都是一樣:讓家族香火永存。除了經營義莊、義田,和其他有勢力家族的「聯姻」也是維持自己家族權勢的方法之一,結合彼此的政治力量、社會資源、名望,以壯大自己的聲勢。然而,不幸的是,宋代家族雖然可以用這些方法努力維持自己的家業,但這並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政壇情勢詭譎多變,任何人皆會有失勢的一天;科舉競爭日益激烈,即使比一般平民百姓占更多的優勢,也不能保證每個子孫都能成材。這是宋代家族和之前的世冑門閾的不同之處,也因此我們在宋代看到了比以往各代更多的社會流動,而這是由科舉制度所帶來的可能。
~ 參 考 書 目 ~
1. 傅樂成,《中國通史》下冊(台北:大中國圖書,1996),第二十、第二十二章。
2. 賈志揚,《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1995),第二章至第七章。
3. 詹森,〈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收入陶晉生等譯,《唐史論文選集》(台北:幼獅,1990),頁231-339。
4. 黃寬重,〈科舉、經濟與家族興衰:以宋代德興張氏家族為例〉,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化大學出版部,1996),頁127-146。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六] 宋代家族
[b][size=150][color=blue]宋代家族[/color] [/size][/b]
自從宋代科舉制度成為政府選拔良才的主要途徑後,一般民間仕子藉著應科考、取得官職,提昇自己社會地位的機會也比以往要來得高。但另一方面,這也意指士人在崛起政壇後並不能從此就高枕無憂,若後代子孫幾輩未通過科考取得功名,那前代所積累下的權力、財富可能就會隨著時間而慢慢消逝。因此,宋代士人在功成名就後,如何繼續經營家業、使家祚永存,就成為後代史家極感興趣的一個主題。
在研究宋代家族時,范仲淹所設之「范氏義莊」常被視為是一個「典範」而被人討論,原因可能是因為它在後代成為其他家族仿效的對象(「自范文正公創立義田,遂為千古贍族之良法」1)。但即便如此,由於「家風」的不同,經營家族的方式也互異。若以此為前提,范氏義莊充其量也只能視為是眾多樣本中的一個,並不能完全說明宋代士人用以經營家族的手段。因此,本文擬以陳榮照所撰之〈論范氏義莊〉,以及黃寬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科舉、經濟與家族興衰:以宋代德興張氏家族為例〉,以上等三篇研究報告為資料,作為討論在科舉制度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下,宋代士人如何在此制度的影響下,運籌帷幄,維持其家業而不斷絕。
[b][color=red]范氏義莊 [/color][/b]
范氏義莊成立於皇祐九年(西元1049年),為范仲淹知杭州任內,於蘇州吳、長兩縣購田千畝所設。義莊中設有義田,以田地收穫供養莊內族人;並設有義學,由義莊聘請老師任教,鼓勵族中有心向學子弟就讀,義學經費也是來自義田的收入。
范仲淹成立義莊的原因很簡單,主要是因為他在功成名就後,眼見族內親友多貧寒,和其早年貧苦經歷相比,使其心有所感,為了不讓族人再遭遇同樣的顛沛流離生活,才有成立義莊的舉動。陳榮照在論述范氏義莊成立原因時,除了以范氏早年經歷作為說明,還另外提出宋初流行於思想界的意識型態作為解釋:唐代安史之亂以及接著而來的五代十國亂世,使「地主的統治及當權者個人家庭的地位均呈不穩狀態」2,因此宋代理學家開始倡導重新家族制度,作為安定社會的方法。如程頤、張載便主張恢復周代的「宗法制度」,「以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並可使「人知尊祖重本……朝廷之勢自尊」3。但張載、程頤也並非完全仿造古代宗法制度,如他們便曾提出「奪宗法」4,主張由官位高的族人取代原來的宗子,領導家族,改變了過往專以嫡長子作為繼承人的傳統。然而筆者認為即便這些理學家的意見可用來說明宋代士人「收族」的風氣,但在論述一家族興衰時,還是應以個人動機作為研究起點,否則易給人社會集體意識影響個人行動的錯覺,忽略了個人意識、利益在宋代新家族型態的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
范仲淹在成立義莊後的隔年,由制訂的義莊法規。范仲淹最初提出的要項很簡單,要等到後來其他族人在經營義莊時視實際需要隨時修訂,才漸告完備。從陳榮照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此法規的制訂,是使范氏義莊可綿延不絕近千年、至清末仍不衰的的一個主要原因。在這部義莊法規中,詳細規定義莊經營實施要點,包括義莊的周濟對象、米糧的發放標準(依性別、年齡而有不同)、嫁娶喪葬等重大事宜的輔助費用數額,以及義莊掌管人的挑選、權責等事項都有規定,使後代族人可依例而行,免去朝令夕改、令因人異的弊病;也有「不可典賣田土」、「不得取有利債負」,等規定確保了義莊資產的完整性,免去有不肖子弟將義莊經費挪做他用的可能。此外在義莊法規中,我們也可發現有資助赴京應科考子弟以及贊助義學的條款,總和前面設立義學的敘述,一方面可發現范氏義莊對於推廣子弟教育也不遺餘力,二方面也可發現科舉考試仍被視為是維持家業的一項重要途徑。
此外,作者也提到在范仲淹死後,范氏族人曾上奏英宗,請求皇帝應允州縣官府協助治理義莊子弟違規事項,並得皇帝恩准,使義莊成為政府承認的組織。而在宋元興替之際,以及在清代,都有范氏子孫向政府提出申請,希望協助義莊繼續運作,由此也可發現獲得政府支持也是范氏義莊家業可維持數百年而不墜的一個原因。
最後,在結束此部分的論述之前,筆者認為作者在寫作〈論范氏義莊〉是有些佈局上的缺失,使此篇文章顯得不盡完滿。首先,作者純粹從制度面著手,討論范氏義莊的經營,卻沒有提及其他使范氏義莊經營歷久不衰的原因,容易給人范氏一族在義莊成立後,是個只知「圍爐取暖」、「近親繁殖」的家族團體的錯覺,未能窺見此一宋代家族發展的全貌。第二,作者曾經提到范氏義莊於明代時曾遭逢發展上的挫折,卻未對范氏義莊如何度過此困挫、轉危為安的關鍵詳加說明,不免令人感覺草率。最後,作者認為此種型態的家族組織造成了傳統中國的零散分割,強化小群意識,成為中國社會邁向近代化的一項阻礙。但筆者認為,與其從此角度批評傳統中國家族制度,不如從未何中國政府後來未能在更進一步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來瞭解,這樣或許可發現此種家族型態的興起,有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中央無法將其統治觸角深入地方所間接促成。
[b][color=red]四明袁氏家族 [/color][/b]
四明袁氏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學術家族,其奠基最早可溯自北宋袁穀、袁灼父子兩代先後於仁宗、徽宗在位時考取進士,任政府官職,為家族的興起打下基礎;之後歷經三、四代的中衰,至五、六代的袁燮、袁甫次第中第後才又見復興,其家族壽祚長達兩百年,是宋代另一極富代表性的家族之一。
根據黃重寬的研究,四明袁氏一族用以維持家族地位的手段主要可歸納出有兩點:一是藉科舉入仕,維持家族的政治地位。從第一代袁穀至第九代的袁士復,幾乎每一代都有族人取得功名,長期有族人活躍於政壇,是使袁氏一族即便經歷第三代、第四代的衰敗,卻依然能東山再起的一個主要因素。二是藉由「聯姻」。在作者所收集到的資料中,可發現出袁氏一族締結婚姻的對象主要有兩類:在選擇媳婦時,多以地方仕紳、富豪之女為對象;而在為女擇婿時,則多嫁以新進士人。和地方富族締結姻緣,從袁家的角度來看,是他們可藉此獲得一定程度的經濟支持,以抒解家道中落時的經濟困境;而從富豪的角度來看,可發現和知名士人聯姻可能是他們在事業有成後,用以提昇自己社會地位、名望的手段。而選擇新進士人為婿,一來可能是眼見其未來政治發展上的潛力;二來可能是起因於兩宋交替時的政治混亂,意見相左的朝臣結黨互相攻擊,若在朝廷中尋求支持,可能會為自己家族招致禍害。
在觀察四明袁氏一族的發展時,特別令人注意的一點是,他們並不以廣置田產、厚植經濟實力作為家族發展的手段。除了一、二代袁轂、袁灼曾添購田畝四千頃外,之後幾代,即便已位居高官,仍以清廉自任,未嘗有大舉擴充家業的手段。相反地,袁氏一族是將其大部分的精力投注於學術的研究上,袁轂、袁灼即以詩文名世;之後的袁坰、袁文雖然未曾考取功名,但仍然專注於學術研究,也不偏廢子弟教育,即便家境困難,仍堅持延聘良師,以使子弟能受教育;之後,袁氏在袁燮、袁甫等兩代復興,仍是不改其對學問的熱忱。而家族所來往對象,也多為學者之流。這樣的努力,使四明一地,成為南宋理學發展的重心。而袁氏一族,也因為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而以書香世家知名於後代。
最後仍要提出幾點疑問。首先,黃寬重認為自科舉制度成為入仕的主要途徑後,魏晉以來的門閾觀念逐漸消除。但從四明袁氏一族締結婚姻的對象看來,不論是當地富豪或是新進士人,這些人在政治、經濟上較一般平民百姓仍佔有一定程度的優勢;富豪之所以會和四明袁氏一族聯姻,也可能是因為這可連帶提升其社會地位。從這種角度來看,我們仍然可以發現,財富、權力以這種方式在進行著某種程度的交換,說是魏晉以來的門閾觀念已然消除不如說是另一種講求門當戶對的心理逐漸開始發展。第二,作者以袁燮一房在入元後逐漸沒落,作為袁氏家族史論述的結束,以此未免顯得倉促。袁氏一族本來就不是以厚植經濟勢力作為家業發展的主要基礎,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家族在元代的沒落?是因為無人再中科舉,或是因為戰亂導致這個家族的崩潰?且作者曾經提到孝宗末年,史浩曾在覲縣一地連同其他急公好義者成立義田莊,但卻為對此組織的發展在多做說明,讓人讀時不免有莫名其妙之感。
[b][color=red]德興張氏家族 [/color][/b]
德興張氏一家興起於張偕,而真正奠定家族發展基礎的卻是其三子張潛。根據黃寬重的研究,張偕原本計畫讓張潛也準備科舉考試,但張潛為避免增加父兄的負擔,遂決定放棄應舉的機會,改隨父親經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宋代家族發展的另一個模式:將家力專注於某幾個子弟的培養上,而讓其他子弟另從他務),但這卻無意成為張氏一家發展的契機:張潛大大現出他在營生方面的才幹,使張家成為德興一地的首富。
和之前提過的四明袁氏一族相仿,德興張氏一家也以教育子弟、鼓勵應科舉,以及和其他地方名士聯姻,作為擴展家族勢力的手段。但在黃寬重的這篇文章中,我們又可獲得不同於上面兩篇研究的訊息,有助於我們理解宋代家族發展的途徑。
首先,張潛在致富後,努力收集圖書,建立地方圖書館,並設置學舍,除了作為張氏子弟學習用功的場所,也邀集鄉里中其他聰慧的小孩一同讀書。這一方面有助於張氏地方名望的提升,也是張氏建立地方關係網絡的一個重要方法。如黃寬重所述,這些士族子弟在飛黃騰達後,多對張家抱有感恩之意,雙方建立良好情誼,甚至發展出聯姻關係。第二,張潛也極力塑造家族倫理形象的塑造:努力表現孝悌,照顧兄弟、親姪;並急公好義,熱心地方事務的推行、救濟貧窮,致力於家族地方形象的維護。
由上述可見,德興張氏一家的成功,除了藉科舉制度使家族得以活躍於政壇,並藉此廣結政治勢力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它積極經營它在地方上的影響力:不只將焦點擺在家族成員的發展,更是主動投入社會,參與社會活動,為自己贏得地方望族名聲,而這也成為後來明清地方仕紳興起的一個濫觴。
[b][color=red]總 結 [/color][/b]
以上對三篇文章進行的整理,可使我們發現宋代士人是如何經營、維持其得來不易的家業;也使我們瞭解一地方家族在事業成功後,可能會利用哪些方法來使自己家族地位更上層樓。針對以上三篇論文的分析,並不是企圖清楚劃分出幾種宋代士人族經營的模型,而是為他們所可能使用的策略作一說明,這些手法可能是互相交錯使用的,只是因經營者的不同,而各顯出其特色。對宋代家族進行研究,並不是試圖去建立出一個個的「典範」,而是試圖去瞭解這些士人家族在面對科舉制度所造成的社會流動時,會利用哪些方法去鞏固自己苦守十年寒窗而好不容易換來的權力地位。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人類在面對時局變動時,為了掌握己身命運,所展現出來的強烈企圖心。
~ 參 考 書 目 ~
1. 陳榮照,〈論范氏義莊〉,收入《宋史研究集》,第十七輯,頁427-452。
2. 黃寬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收入《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頁105-131。
3. 黃寬重,〈科舉、經濟與家族興衰:以宋代德興張氏家族為例〉,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化大學出版部,1996),頁127-146。
4.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台北:弘文館,1996),第七至八章,頁111-149。
5. 袁采,《袁氏世範》。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七] 婦女
[b][size=150][color=blue]婦女[/color][/size][/b]
婦女史研究是隨著近代女權思想發展而逐漸形成的一門學科,學者欲打破傳統以男性敘事觀點為中心的歷史研究,重新建構過去,以顯現女性向來在歷史上不被重視的地位。但在古代中國歷史纂述多由男性史家執筆的情況下,婦女史史料「編於諸書有可引者少,無可引者多」,要將這一段「隱藏的歷史」重新挖掘出來,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所謂「男主外,女主內」,過去中國婦女多以「家庭」為生活的主要場域。依此角度看來,「家族」不失為進行傳統婦女史研究的一個很好脈絡,而這又可包括婚姻關係、家庭角色、地位等不同面向。
北宋理學家程頤有所謂婦女「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名言傳世,後來史家往往引述此語,認為宋代婦女受極嚴格的貞潔觀限制,夫死不能隨意再嫁,為夫所棄,也不能再另覓他郎。但這種看法卻逐漸為後來的研究者所質疑,認為中國自古即有重視貞潔觀念的傳統,但歷代強調程度不一,雖然宋代也有若干士大夫予以提倡,但宋代婦女貞潔觀仍未普及。在記載宋代婦女婚姻關係史料中,有歌頌婦女守節的紀錄存世,但也可發現有婦女改嫁或再嫁的例子出現。這些記錄婦女生平的資料多附屬於史料中婦女丈夫或子女的文集或傳記,因此儘管是爭議性極大的再嫁或改嫁,也都要藉士人的紀錄才有可能流傳於世,可見這些著者並不以改嫁、再嫁為見不得人的事,否則必不會允許這些資料傳世。
改嫁的前提是丈夫休妻或妻子主動離異。中國自古就有「七出」(五十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盜竊、妒嫉與惡疾)、「義絕」(夫對妻族和妻對夫族的歐殺、姦非)的說法,指出丈夫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宣布休妻,否則在宋代,他必須受「徒一年半」的懲罰;也有所謂的「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持舅姑之喪與先貧賤後富貴)限制丈夫不許與其離異。但「不事舅姑」、「口舌」、「妒嫉」判定標準模糊,予人任何解釋的空間;「惡疾」棄妻顯然有違夫妻之義,顯示出這種標準對女方的不公。
妻子主動宣布與夫仳離在法律上更為困難,主要是來自於父系社會「男尊女卑」對禮法的強調,重視雙方關係中的上下之分。但宋律規定夫挾妻財失蹤,妻無以自給,即可改嫁,和唐律規定夫失蹤六年後妻才可改嫁,已顯較有寬鬆,也可看出對婦女人身權利的尊重。
婦女再嫁原因有很多種,但主要壓力還是來自現實生活的考量。若夫家不願意照顧寡婦的經濟生活,自己又無力更生,也只好選擇再嫁。父母對於歸家的女兒,也可能基於情感上的需要,鼓勵再嫁,使女兒有所依靠,精神上有所寄託,也可得到一定的保護。
但這種情況到了後代逐漸有所轉變。明清兩代是中國極強調婦女操守的一個時代,政府此時也大力提倡。但觀察一些自宋代逐漸發展出來的社會現象,我們似乎也可發現一些端倪,說明明清兩代對婦女貞潔觀的強調,在宋代已有一些脈絡可循。
宋代盛行「財婚」,即兩家聯姻,必先論及聘財、婚奩。古代中國婚姻,原非男女雙方在自由戀愛下的結合,而是兩家族用以擴大社會、政治地位的一種手段。魏晉南北朝以迄唐代,社會上婚嫁首重門閾相當;宋代婚姻論「財」,可說是另一種追求「門當戶對」心態的發展。此種風氣為何發展,原因至今不明,但有可能是士大夫以追求功名維繫家族地位的另一種手段,而後才逐漸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在黃寬重先生研究的「四明袁氏家族」中,袁氏一家在子弟於考場失利時,便藉著與地方富室女聯姻,如袁坰娶四明富家林氏之女為妻,袁文妻戴氏之祖戴侃為鄞縣財主,以維持家庭地位;這些地方富豪和士人子弟聯姻,一方面是欲藉此抬高身價,另一方面也是看重這些士人在通過科舉後,隨著一官半職而來的政治、社會權力。在〈袁氏世範〉中,我們也可看見袁采諄諄告誡家中子弟,「凡事不可不早慮……至於養女,亦當早為儲蓄衣衾妝奩之具,乃至遣嫁,乃不費力」,否則到時候「臨時鬻田產,及不恤女子之羞見人也」,借高利貸,賣盡田產,或徒留婚嫁失時之憾。又或女兒幸而出嫁,嫁資不足,也會影響其在夫家的地位。受丈夫、舅姑喜愛,或為人嫌棄,和女子的嫁妝有極大的關係。也因此宋代常有嫁女之資超過娶媳費用的情況,反應社會現實的一面。
宋代已婚婦女對其妝 有相當程度的支配權力,若未經允許,丈夫基本上是不可以隨便取用。從上述宋代婚姻重財的風氣來看,婦女嫁資常不是一筆小數目,對夫家經濟狀況必有相當程度的正面影響。但若夫死,面對寡妻的可能再嫁,那夫家又應如何因應?且嫁妝和夫妻婚後營置的產業依法律規定,都屬於夫妻的「私財」,與家族的「共財」無關。因此,寡婦若於夫死後歸回本家,又或另行改嫁,對夫家來說,必會造成影響;且子弟隨著寡母再嫁於人,是逐漸重視家族觀念的宋人所無法容忍。在這些現實情況下,對婦女的守節不再只是單純在禮法規約上的強調,且也開始有其實際上的考量。
雖然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然而,從許多宋代士族婦女都是知書達禮的溫婉女性看來,這種說法並不確實。而在宋代科舉制度孕育下逐漸形成的士大夫家族中,婦女也確有接受教育的必要。宋代士人,為了追求功名,常必須埋首於書堆;而在求得功名後,或是到外地任官,或是專注於官場上的競爭,常無暇教育子女,治理家事。為了維繫家庭的興盛,婦女便必須替代夫職,料理家務,替丈夫為家中的大小事盡心盡力,這就要求婦女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水準,才能勝任這些工作。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論財婚姻風氣盛行的宋代,是否具有一定的「德智」成為士族揀媳娶妻時的另一項重要條件。
從平民的角度來看,女性,在古代中國以農業為生活基調的社會中,無疑是協助生產的一項重要勞動力來源。「男耕女織」,婦女在農業生產之外,進行副業的經營,也要在農忙的時候,下田勞動。這也使一般市井小民不會隨便放棄他們的伴侶;即便夫死,妻留夫家,仍是一重要人力來源。
一方面基於經濟上的考量,另一方面又考慮到婦女在家中的角色,遂使強調婦女守節除了維持基本禮法秩序外,有了更實際的需要。宋代時,城市經濟發達,新產業也逐漸發展,使得宋代社會的職業分類有了更多元的變化。婦女投入生產,也使其經濟能力提高。她們可以獨立謀生,無須仰賴他人而活,有利於她們夫死守節,為因有感於伉儷情深、不捨公婆、不使子女無宗而欲從一而終的婦女,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中國傳統社會對貞節幾近病態的強調是至明清才有的現象,雖然宋代已可發現些許跡象,但從文獻中仍可有婦女再嫁、改嫁的例子看來,宋代仍處於一種社會階級仍在發展的社會,允許任何可能性的存在。而從婦女對家庭功能的重新發現,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古代女性並不是完全看不見的一群,她們仍在男性宰制的社會中,默默地發揮她們的影響力,只待我們定睛注意。
~ 參 考 書 目 ~
1. 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台北:弘文館,1986),第八章,頁129-148。
2. 陶晉生,〈北宋婦女的再嫁與改嫁〉,《新史學》6卷3期(1995),頁1-26。
3. 陶晉生,〈北宋士族婦女的教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年3月),頁43-58。
4. 柳立言,〈田宋代婦女的守節與改嫁〉,收入《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輯,頁143-183。
5. 袁采,《袁氏世範》。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八] 城市、貿易、工商業
[b][size=150][color=blue]城市、貿易、工商業[/color][/size] [/b]
宋代城市工商業貿易的興起其實早在隋唐時就已奠下基礎。首先是隋唐時開鑿的大運河成為連絡南北的重要媒介,在當時交通運輸仍大部分仰賴漕運、陸運的中國實有重大意義。因為這使得生產於不同地區的物產、資源得以便利地在幅員廣大的帝國境內流通,降低了長程運輸所的不便以及時間成本。其次是中唐以後中國的戰亂頻繁。表面上看起來戰爭造成了人民的顛沛流離,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卻具有促進中國人口遷移的積極意義:中國人口聚集中心因北方戰亂不斷、人口大量南徙而移至南方,為當時仍地廣人稀的南方帶來開發所需的人力、物力。至宋代時,南方已超越北方,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
原本,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以滿足本地所需為主,即維持在自給自足的層次上,少有以地區為單位,進行跨區域性的大規模經濟交易活動的出現。但在宋代時,中國的經濟卻逐漸發展成一全國性經濟市場體系,各地生產物品在帝國境內互相流通,地區之間的互賴性增加,各地的經濟規模不再只停留於自給自足的層次;甚至其他鄰近國家如遼、西夏、日本等也被納入於此一經濟體系。這種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當時中國生產型態的改變有關,其中又以稻米的耕作為主要因素。
即便中國很早就有植種稻米的紀錄,但稻米其大量生產、甚至供成為廣大中國人民的主要糧食,卻是要到宋代才發生的事。這主要是因為稻米這種集約作物在收割前亟需大量的人力投入,從事栽種、灌溉、防害等工作,而之前中國人口又主要是集中在北方、缺乏人力所致。但如之前所述,中唐後逃避戰亂的人口大量南遷,為南方這片廣大土地帶來開發所需人力,使稻作的大量栽種成為可能:再加上當時農業耕作技術的進步、水利灌溉的發達,稻米產量遂大量增加,成為南方中國的一項主要作物,除了滿足本地的需要外,也有餘力供應外地的消費。
稻米的大量生產逐漸產生兩項影響,一是促進地區專業化農作的產生。農業生產一方面本因地區自然條件的制約而會有物產種類的差異;再加上各地開發情形不同,即便生產相同物種,也會有產量高下之別。稻米大量的生產,打破地區自給自足的傳統,原本不利於生產稻作的地區因可以獲得其他稻作區供應、滿足糧食需要,遂放棄作物生產,轉而種植、發展適合地區特性的作物、產業。宋代時,一方面「蘇常熟天下足」、「蘇湖熟天下足」諺語的流傳,顯示蘇湖一帶稻作栽培的發達,部分地區豐年的收穫即可供應全中國其他地區的需求;另一方面,自「洞庭柑橘最佳」(龐元英《文昌雜錄》)、「今棉州乾薑為天下第一」(《嘉泰會稽志》卷十七)、「今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溫州、惠州,皆知名。」(蔡襄《文房雜評》)等紀錄,以及太原葡萄、河陽查子、趙州桃、河陰石榴等在物產前掛上生產地的用法,地區物產專業化生產的情形可見一斑。
然而,上述現象在宋代的出現並無法單獨存在,還有賴於「交通運輸」此項重要條件,否則便無可能。因為如蔬菜、水果、米糧等不易保存的物產,在收成後必須盡快運送至消費地,一旦腐壞,便損失不貲;而如木材、礦產之類較笨重的產物,更是需要便利的交通運輸運送,否則耗時、耗力,便無法有效達成跨區域性的交換。宋代時,隋唐開鑿的大運河仍繼續發揮作用,成為溝通南北兩大地理區之間最重要交通管道,許多地方物產就是藉著這條便利的漕運而能南北互運,發揮互通有無的功效。「柴米油鹽醬醋茶」等在前代仍不甚普及的物產,至宋代遂成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開門七件事」(明田義蘅《劉清日扎摘抄》卷二〈七件事〉),便是在物產豐富、交通運輸順暢下,逐漸發展出來的社會景象。此外,更有許多物產,是因運河輸送至南北的集散地,再經由外國行商之手而散佈至外國各地,如宋代的香料、絹、藥品、顏料等便曾進入日本。就這樣,隨著稻米生產的增加,成為中國廣大人口的主要食糧;地區專業化產業的興起、形成;再加上便利的漕運輸送,中國各地區之間的互賴程度增加。在宋代,一個前所未有的全國商業市場於焉成形。
此外,隨著地區間物產流動性的增加,一些人民平常為交換日常生活所需而形成的村落集市也開始產生變化:一方面隨著日常需求的提升,新的集市陸續出現,交易頻率、時間也增加、延長;另一方面,原位於各交通要道的集市的重要性也開始增加,逐漸從一地區交易點發展成為村落,甚至是鎮、縣等規模更大的行政單位。以往,中國的城市功能多集中在政治行政上—即中央政府設置地方行政單位的目的只是為方便管理地方事務。但宋代時,開始以商業為目的的城市開始陸續出現,這些城市發生地點多半是交通要衝,或是地區貨物集散點;功能主要是進行工商業交易,生產功能變成次要、逐漸分散至鄰近較小市鎮。以一主要城市為中心,周圍散佈著大小不一的地方城鎮、村落,兩者結合成了一城鄉網絡,發揮城鄉分工的功能。加上唐以前市坊分離的限制開始瓦解,城市商店、住宅林離雜處,今日城市生活樣貌逐漸形成。
米糧大量生產的另一項影響是農村生產人力的解放。稻米是種可以供養大量人口的作物,維需仰賴許多人力長時期的投入。宋代中期以後,一方面稻作的集約化、精耕化加強,糧食的大量增加使人口比例逐漸上升;另一方面,由於土地兼併的情形逐漸嚴重,使農村每戶所有耕地狹小不均。這些情形所造成的影響即是農村所需人力瀕臨飽和,許多人家在務農之餘,或許也從事零星副業,以維持家計;但有更多的農村人力選擇放棄務農,轉向發展其他產業,促使農村人口開始往工作機會較多的城市移動,導致都市人口的集中。
斯波義信在研究宋代的商業與社會時,曾指出中國傳統「士、農、工、商」四民的職業分野在宋代已然崩潰,逐漸有所謂「八民」的說法產生1—即於原來的士、農、工、商之外,再加入佛(僧侶)、老(道士)、兵(應募兵制而進入軍隊服役的人民,以俸米換取現金,或經營小本商業)、游手(農村剩餘人口,從事私販、賭博等業,可能也包括一般販夫、短工、屠夫)等四階層民眾,可見宋代因農村因可耕地的有限,其他人民不得不已其他職業為職,使古代中國的職業分化更趨複雜。
在城市中,工商業往來繁忙;而在城市外圍,也多有交易市集的聚集。商客往來頻繁,可說是熱鬧非凡。此時,為了管理商業活動,許多同業商人仍沿用唐代習俗,設有「行會」組織,以便監督、控制行內事務,也代表本行商人和政府進行交涉。而為了便利遊走各地客商的需要,城市中有多有邸店的經營,供其停留、休息。
隨著貿易的發達,城市財富的累積,一般市井小民也開始注重閒暇時的消遣。宋代城市中有以「勾欄」或「棚」為中心的瓦市的出現。瓦市原意為臨時市集,後來變固定成形,其中除了一般市集,也有飲食店、酒樓、茶坊,供民眾消費。有些瓦市設有「勾欄」,街頭藝人表演場所,以娛樂一般市民。
為宋代城市生活留下最好紀錄的作品無疑是北宋張澤端的畫作:「清明上河圖」,以當時汴京繁忙市景作為創作題材。在畫作中,我們可以看見城市建築的雄偉;也可看見各種不同職業的人在城市中遊走,如道士、僧侶、文人仕子、等;也可發現當時城市生活之繁榮。透過畫家精細的筆觸,栩栩如生的描繪,在畫作的幫助下,思緒彷彿又重回一千年前的宋代,親身體驗當時城市生活的繁華,歌舞昇平。
~ 參 考 書 目 ~
1.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台北:稻禾,1997),第三、第四、第七章。
2.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下編:二、唐宋之際都城制度的重大變化〉。
3. Valeria Hansen (1996): The Beijing Qingming Scroll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c/o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at Albany, NY, 12222, USA.).
最後由 小地震 於 2004-05-24, 17:36 編輯,總共編輯了 1 次。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九] 農村、土地、租佃
[b][size=150][color=blue]農村、土地、租佃[/color][/size][/b]
「部曲」一詞原是軍隊用語,意指部隊,但自東漢末年起就被用來指一群在有勢力豪門貴族的莊園土地裡為其耕作的一群人,是中國中世紀特殊社會背景所造就出來的一群特殊階級的人。一般平民百姓在亂世中無從歸依,只得依附在豪強勢力底下,換取自身的生存,這些人就被稱為「部曲」。他們在豪強的莊園中耕作,也為莊園主提供勞役上的服務;而莊園主則是藉著提供保護來換取這些人的忠誠。至唐代,社會景象雖然承平,但如同魏晉南北朝門第餘風仍無法去除,部曲此特殊階級仍然存在於唐代社會。貧民生活無以為繼,便可投靠有勢力的人,以換取衣食上的溫飽,這些人最初被稱為「衣食客」,後也逐漸以「部曲」稱之。部曲和「奴婢」不同,擁有較大的人格與自主權,但在唐代,他們同被劃為是「賤民階級」。
但經歷唐末五代的戰亂、變動,隨著制度上的更改、社會背景的演變,部曲這群在唐代被劃為賤民階級的一群人,逐漸開始消失。莊園的經營原本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但此種背離經濟互通有無原則的生產方式只是地主為了確保自己的產業在經濟不景氣、貨幣經濟停滯的社會中能夠繼續保持所想出的一個權宜之計,必終將因社會的安定而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適應各種土地條件的生產專門化。其次,唐中期後因為租庸調法的廢置,由楊炎新創立了「兩稅法」,將力役、土地租稅等合併,分於夏秋兩季徵收;不論土地歸誰所有,一律按耕地面積納稅,等於是變相地承認土地私有制度。而隨著中唐之後的戰亂,原本的北方貴族勢力也開始沒落;中國人口中心移至南方,隨著農產品有逐漸商品化的趨勢,釋出大量農業勞動力,轉而投入其他產業的生產,使工商業也開始發展。以上種種現象的出現,暗示的是人民(部曲)逐漸從徭役勞動中解放;工作機會的增加,除農業生產外人民可選擇其他謀生方式,不再以務農為唯一依歸。因此,「部曲」此一階層便逐漸消失,成為一歷史名詞,取而代之的是「佃戶制」在宋代社會的興起,佃人自願向地主承租土地耕種,建立一種互相的契約關係;在商談的過程中,地主屢次尋者適合自己條件的佃人,佃人也以地主提供的條件決定是否承租。雖然地主佃農兩者之間仍有地位高下的差距,但這種地位上的不平等是取決於經濟地位的高下,而非如唐代社會的身分階級制,如宮崎市定所說,宋代是一個身份制消滅的社會1。
但這是否就代表一向佔中國人口比例絕大多數的農民的生活境況得以改善呢?從歷史的紀錄上來看,很顯然情形並非如此。宋代稅目之雜,課稅之重,為前代所無。宋代仍沿襲唐代舊例,行兩稅法,這原已包含租庸調法中的「庸」,即勞役部分;但宋人仍必須負擔政府差役,可見其負擔之重。而且宋政府還將五代時南方諸國為取利人民所徵收之「身丁錢」劃為國家正式稅收的一部份,規定凡南方年滿二十歲至六十五歲的成年男子都要繳納,也深為百姓所詬病。
國家稅收本應由每個國民平均負擔,但宋代存在著無需納稅的某些特權階級,如官宦士太夫,或是有某些階級人民可免於某些賦稅的課徵,如太學生、得文解人等免於繳納上述之身丁錢,單丁、女戶等免於服勞役…,造成民間賦稅分攤不均。國家真正的收入多集中在官宦、富豪之手,但這些特權階級不是有免於納稅的特權,就是懂得如何避稅,使國家大部分的稅捐要由一般平民負擔,造成明顯的不公平。也有因官吏執行不當,而使人民必須負擔多餘的賦稅的情形。北宋中葉以後,由於力役、租稅的繁重,逐漸有農民棄田逃亡的現象,或是有小農自願將田地獻於豪強,降己身為佃戶,以逃避重稅壓迫,使土地兼併問題日益嚴重。且豪富常在穀物收成之時,壓低市價,農民為了趕緊繳稅、償還債款,只得賤賣稻糧、變換現錢;富豪利用此機會囤積貨物,至飢荒、米價上漲時再趁機賣出。以上種種情形,在在都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宮崎市定並指出,在保護佃戶地位、不許地主干涉佃戶轉移,以及維護地主利益兩種矛盾情結下,宋政府有逐漸朝保護地主權利的方向走去,允許地主可對佃戶施行某種程度上的暴力2。而事實上,為了求得存活,農民也不得不依賴地主,唯地主之命是從。因此,宋代一般農民生活情景之悲苦,可想而知。
然而,眼見此情景,宋政府難道真的沒有試圖去改變人民的生活狀況嗎?當然還是有的,北宋時期,范仲淹、王安石先後於慶曆、熙寧年間推行的兩次變法改革中,就有改善農業生產、維護農民生活的具體措施;而在南宋,即便沒有人在北宋接連兩次變法失敗後再推行大刀闊斧式的變法,但小規模的改革還是有的,如李樁年、朱熹等人在南宋時曾推行土地經界的釐定工作,企圖以此平均土地租稅。然而,以上改革不是以失敗告終,就是只能小規模地推行,無法真正全面地改善農民生活。原因何在?其實答案很簡單,改革推行時,常因新法內容干犯到既得利益者的權利,引起反對;或者是因為在下推行的人不具有足夠知識,或無法體察在上者變革心意,因此推行不力,甚至有失當的情形發生。而後者更給反對者反對的藉口,使得良法立意雖美,卻無法徹底實行,百姓生活依然如故。而如之前所提之身丁錢,雖被視為是苛政,卻於兩宋遲遲未能全面廢除,是因為宋代國庫消耗大,因為冗官充斥,為以厚祿養連;北方外族威脅未減,以增兵作為抵禦之道,軍費沈重;幼胃維持和平,每年必須奉上大量求和歲幣,使宋代財政時時都面臨窘境,也因此秕政不但無法廢除,還要以增加賦稅作為維持財政平衡的手段。
政府無法解決人民問題,社會自然百病叢生。為了逃避沈重稅賦、力役,人民往往棄田留徙;或是怕因財產過多,被選為里長、保長,負擔沈重差役,而不敢努力增產;甚至有人家為求成單丁、女戶,以分家析戶作為逃稅手段,甚至隱瞞戶口不報;也有人家自願將自己的孩子送往寺觀為釋道,甚至有溺嬰的惡行出現。以上都是民間為逃避重稅而延伸出的一種因應之道,可視為是百姓無力改變生活現況而對政府統治提出的一種消極的抗議,也使人深切感受到在無能政府統治下人民生活情況之淒涼。
~ 參 考 書 目 ~
1. 宮崎市定,〈從部曲走向佃戶〉,收入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五代宋元》(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71。
2. 王得毅,〈宋代身丁錢之研究〉‧收入其《宋史研究論集》(台北:商務,1993),頁197-251。
3. 王得毅,〈李樁年與南宋土地經界〉,《宋史研究集》,第七輯,頁441-480。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十]
[b][size=150][color=blue]新儒學的興起[/color] [/size][/b]
新儒學,或稱「理學」、「道學」,指的是發生在兩宋之際,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重新受到肯定的復興運動。雖然此一名詞用來專指宋代的某些知識份子,但這種學術淵源最早卻可回溯至中唐時的韓愈。韓愈當時在文壇上發起古文運動,反對文藻華而不實的寫作方式;提出反對佛老思想的主張;鼓勵學者重新回到孔、孟學說,肯定儒家學術在穩定政治、維持社會秩序上所具備的功能。這種主張為兩宋時代的學者所蹈襲,並將之發揚光大,成為新儒學學者的普遍主張。
韓愈在當時之所以會發起古文運動、反對當時社會普遍崇尚的釋、道思想,和當時國家社會歷經安史之亂、胡人所激起的動盪不安,夷夏之防的漸趨嚴厲有關。而宋代有心於改造國家社會的知識份子所面對的局勢,和韓愈相較之下,卻是更為艱難。在兩宋三百多年的歷史中,國家始終無法免於外敵所帶來的威脅。外族的交相逼迫,激起了士大夫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他們一方面極力推崇中國傳統道德學術思想,以和當時仍流行於社會上的佛老思想相抗衡;另一方面也試圖在論語、孟子、六經等古聖先賢的諄諄教誨中,尋求經世濟民的治世思想。雖然這些新儒學思想家強調要重拾古代經典,拋開古人注疏,以今日的角度重新詮釋這些古代典籍;但因為每個人對古代典籍的理解不同,所強調的重點也互有差異。北宋新儒學學者胡瑗認為先王之道有三:一為「體」,指的是仁義禮樂等亙古不變的原則;二為「用」,指如何將這些先聖先賢的教訓、原則(體)實際地運用在國家的統治上;三為「文」,即是古聖賢傳於後世的典籍之作。這為我們在理解兩宋之際各學派、不同新儒學學派思想家所提出的改革時事之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法:雖然思想根源皆來自孔孟古語,但因為每個人的理解不同,也連帶影響他們將之實現的方法,即在「用」這點上,表現出極大的差異。
北宋王朝以「強幹弱枝」為國策,政策的具體運用表現在大開科舉、重用文人上,使北宋知識份子得到比前朝文人更多機會,可在政壇上一展抱負,實現其經世濟民的理想。北宋兩次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均是將理想付諸實現的具體行動。慶曆變法時,改革派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希望從「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勵行法治」等方面下手來引導宋廷走向富強之路;神宗年間王安石所主持的激烈改革計畫,原則上也不脫范仲淹政改時所提出的幾項主張,只是在政策實行上提出更為具體的措施。其中兩人也都提出了改革教育的計畫,針對當時科舉考試只強調應試者的文學才能、而不重視實際治世能力與人格操守的弊病,提出科舉改革方案,也希望能藉著逐漸擴大學校教育的功能,來取代科舉這條為國家選拔人才的管道。
這兩次的變法最後都以失敗告終,且都在北宋政壇上引起不少風波,特別是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更在無意中將北宋帶往衰亡一途。政治改革危害某些既得利益者權益,使保守份子起而反對新政,甚至使政治陷於混亂可能是這些有心於改革政治的知識份子當初所始料未及的;但在這裡,欲向讀者強調的,是這些獻身於政改風波知識份子的學術背景:他們大部分都是儒學在宋代的支持者,即便是後來深為新儒學學者所排斥的王安石也不例外。
王安石奉《周官》為改革規臬,其對土地改革的理想和程頤、程顥、張載等宋儒學者的看法有相同之處,皆肯定古代的兵農合一制度。但在具體實施上,張載認為均田制的實施勢在必行;程頤則顧慮到可能會有人反對,因此不強調以強制手腕來達到政策的實行,否則便是背棄「王道」,落入「霸道」的批評中。但對於此,王安石本人並不認為此古老制度有在宋代這塊土地上實施的可能,即便他自己也是均田制的信奉者。相反地,王安石採取其他措施,如減輕農村貸款、控制市場機制,以間接的方式來實行其理想。但他這樣的方法卻為其他改革者的反對,認為「青苗法」、「市易法」等政策圖利於民,非先王之策;但從王安石的眼裡看來,這不過是使制度得以「永續經營」的一項必備措施。政策上的分歧,加上王安石的一意孤行,使得當初原來和他有相同抱負的盟友也漸漸離他而去,使他不得不任用新人,終至釀成後來的新舊黨爭。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在「體」(原則)上的一致,但在具體實施上(「用」),雙方卻因為對經典理解的不同而出現作法上的差異。後來王安石紛紛為日後的新儒學學者指責,被當時的學者排擠於道學學者的大門之外。但從今日的角度來看,王安石的學術思想和當時的新儒學學者其實也有相通之處,他也是當時道學家的一份子,這是我們在論述時必須為他澄清的。
北宋滅亡,有人認為是北宋末年的政改所致,因此在南宋,我們很少發現這些新儒學學者在政治參與上有多大的作為。他們到哪裡去了呢?北宋末年政改引起的激烈黨爭,使得當時在政壇上習慣互相援引、支持的政治人物紛紛捲入黨爭的糾紛之中,影響士人家族的生存。因此在南宋時期,許多知識份子紛紛從中央政治場域中退卻,以地方、家鄉做為起點,經營他們的家族、學術事業。身為儒學傳統繼承人的他們也沒忘記他們所肩負的經世濟民重責大任,因此他們也以地方為場所,來實踐他們的理想。
南宋的新儒學學者,以朱熹、陸九淵為首,可分為兩大派。朱熹的思想以「為己之學」為根本,認為真正的學習是以修養個人德行為根本,並兼可達人;反對以應科舉、入仕做官的教育目標;並強調人在社會網絡關係在個人學習道德知識上的重要性,近似於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的主張。以此為出發點,朱熹一派的學者在地方上紛紛推行「書院」、「鄉約」、「社倉」、「先賢禮」等社會制度、機制的建立:以書院為起點,實踐他所認可的自由教育理想;並藉著「鄉約」、「社倉」、「先賢禮」等社會制度的推行,來建構一個穩定、互助、和諧的地方社會,在中央政府力量漸無法有效控制地方社會的時代裡,發揮安定社會的力量。
而和朱熹一派相當不同的是,陸九淵並未大力支持朱熹所強力推廣的社會制度。或許這和陸九淵對學習的態度「因人設教,直指本心」—亦即對個人致知能力的肯定有關,認為一個人若能致力鑽研古代典籍,沈潛於心,那便可領悟聖人之道(「學笱知道,六經皆為我註腳」)。但Robert Hymes也特別指出,陸九淵之所以不如朱熹一般,致力於鄉約、社倉、先賢禮等社會制度的建立,或許和他的生長背景有關。陸氏家族累世同居,子祚綿延,使陸九淵深以為傲。而宋代家族累世同居、族人互濟的功能,以及家學、祀堂的建立,在功能上和朱熹推廣的種種制度相當,使他無意於另行其他制度的推行;甚至是害怕推行朱熹所推行的制度,將會對他引以為傲的家族制度帶來破壞。
學者普遍認為在南宋時代,國家政府的力量已經無法有效深入地方,控制民間社會,因此地方鄉紳紛紛致力於社區、中央國家之間統治連帶關係中縫隙的彌補,朱熹的鄉約、社倉、書院其實就是前代國家推行的保甲制、青苗法、書院等制度的轉化,以地方作為實施的主導力量;而陸九淵所引以為傲的家族制度,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正好扮演了地方社區的功能,以「社區家族」直接作為和國家政府連帶的基礎。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宋代學者在「體」、「用」上所出現的差異。
南宋末有所謂「道統」的說法的出現,以朱熹一派為首的新儒學思想也在宋末、以迄元、明、清受到政府的肯定與推崇。但在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揚名於後世的新儒學學者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在政治上、在學術上並不能算是主流;他們所代表的,是和當時社會大多數人意見相左的政治、學術意見。即使是朱熹一派,也是在南宋末理宗時才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認。面對當時怯於改革現狀、擔負起國家存亡重責大任的多數保守份子、或是只著眼在個人名望、地位維持的功利份子,他們是「曲高和寡」的一群。但這些新儒學學者秉持著對自身學術傳承的肯定、對知識份子於國家社稷所應有的責任、以及對自己尊嚴、獨立人格的維護,願意挺身而出,猶如螳臂擋車一般地和巨大的君主專制權威、現實的政治利益相抗衡,深知讀聖賢書,應為何事。這樣看起來或許會讓人感到不自量力,但就是有這些懂得堅持自己的「頑固」知識份子的存在,中國政治才能在強調穩定的傳統中,進行緩慢的變遷。雖然後來有人認為兩宋新儒學家所致力維護的道統,為後來君主專制政體所利用,使中國陷入一個幾近保守、僵化的局勢而對這些新儒學學者大肆抨擊,但仍然要為當時仍堅守道德立場的他們,表示肯定。
~ 參 考 書 目 ~
1. 狄百瑞,《中國的自由傳統》,李弘祺譯(台北:聯經,1983),第1-3章。
2. 錢穆,《國史大綱》,第41章〈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
3. 謝康倫,〈論偽學之禁〉,收入《宋史論文選集》,頁159-200。
4. 劉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立〉,收入其《兩宋史研究彙編》,頁249-282。
5. W. Theodore de Bary, “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roject reprint series ; no. 18-19 (1965): 81-111.
6. Robert Hymes, “Lu Chiu-yuan, Academic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Local Community”.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之十一] 宋代宗教
[b][size=150][color=blue]宋代宗教[/color][/size][/b]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巨大變遷,在眾多學者的爭相論述下,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許許多多至宋代中國才出現的現象,如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正式南移、新士族階層的形成、科舉制度的成熟、全國商業市場區的形成等,一方面把宋代和之前的朝代區別開來,另一方面也令許多學者對此朝代另眼相看,視之為近世中國的開端。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所出現的重大轉變,也連帶地影響宋人的宗教生活。宋代宗教最獨特的地方有兩點:一是除原有的釋、道二教仍繼續發展外,有許多新進神祇的出現,將宋人的信仰體系妝點得多采多姿;而和這相關的是宋廷對神祇的賜封也大量增加,反映出政府欲從信仰生活增加對社會控制的企圖。另一是「區域性」神祇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神祇活動地域的限制,而這和宋代全國經濟市場的形成以及兩宋交替之際、大量北人的南遷有關。以下茲分別敘述。
宋代民間信仰的一大特色是新神祇的不斷增加,這和宋人用以判斷哪一神祇值得信靠的標準有關:即是否「顯靈」,展現神蹟,切實地回應人民需求。許多死去的人常因為在某個地方顯了靈,被人發現,而就贏得人們為之建祠堂、進行供奉。這種對「神蹟」的強調,反映出中國人講求「實用」性格的一面。因此敬拜神明,為神祇雕像、修廟,甚至是上書朝廷、請求賜封,一方面是除了表達敬謝之意;另一方面也是「鼓勵」神明多顯靈。若神祇不再顯靈,就會被人民打入「冷宮」,為人遺忘,而被新一個繼之而起的神祇所取代。而是否「顯靈」也為人民在如此多的神祇中提供了一個參考方向:只要是靈驗,就可以信靠,管祂是屬於那個宗教。這種中國人民在選擇信仰時的自由、彈性也可說是一種信仰上的實用主義的證明。
宋代出現的許多新神祇,和之前以古聖先賢、英雄帝王之尊被奉為神祇的情形不同,多半是出身自一般平民。他們生前可能默默無聞,也可能只是一介女流,但死後卻能被奉為神祇。這種情形也和宋代人民強調的「顯靈」有密切關係。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五代兩宋之際,前唐世冑門閾觀念沒落,平民社會漸代前朝貴族社會而起的一種反應。即便是市井小民,死後只要是有功於鄉里人民,也可和先聖先賢、將相豪傑相提並論,同登神位,為人所世代景仰。
即便宋代不是第一個對神祇進行賜封的朝代,但如此大規模對神祇進行封賜卻是前所未有,從北宋中期開始達到高峰,以迄南宋末而不斷。除了數量上有顯著增加,對神祇的賜封有開始制度化,出現了一定考核程序以及相關儀節。而不僅是神祇人受封,這種榮耀也開始恩澤家屬,甚至是其部屬也跟著雞犬升天。這種對神祇進行賜封,一方面表現宋人認為地上政權高於天上神權,即便是高高在上如神祇,也必須服從政府號令;另一方面也顯示政府欲透過控制人民的信仰生活—即鼓勵對某些神祇的影響以及判某些祠廟為「淫祠」而加以禁止—來達到加強社會控制的目的。在政府已普遍被認為無法有效將控制力深入民間社會的南宋,這或許可說是政府欲藉另一途徑來加強對人民管理的一項措施。
當我們在談論對神祇的賜封時,有一群人是我們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在整個過程背後運動的「信徒」。並不是每個向上聲請賜封神祇的請求都會被允許,在同樣一個地方可能會有許多不同神祇共同競爭人民的信仰,以及被賜封的殊榮。因此若想要脫穎而出,神祇的支持者們有無權勢就變成了整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關鍵。在宋代許多可查考到的例子中,有許多都是地方有權勢者要求地方官員為其信奉神祇向朝廷奏請。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兩種互利關係的流動:地方仕紳鼓勵對某一神祇的祭祀,並藉請求為神祇賜封來達到增加地方聲譽的目的;也藉固定地方信仰,來增加鄉里百姓對地方的凝聚力。而從地方官府的角度來看,和這些地方菁英打好關係有利於他進行對地方的控制,為了取得地方菁英的合作,因此以承認當地神祇作為一種回報的方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宋代地方主義的發展。
宋代民間宗教另一項極具意義的發展是「區域性」神祇的開始出現。傳統認為每一神祇都有一固定領地,只有這地區中的人才信奉祂;而神祇顯現神威的地區,也只侷限在他們祠廟所座落的城鎮,表現出強烈的地方性。但至宋代,這種地方性逐漸被打破,開始有人認為既然神力無邊,那其力量範圍也自然不受限制。梓童、天妃、張王等神祇在宋代末年的祠廟遍佈全國,充分地表現出此種神靈觀的發展,而這和宋代全國性市場的形成以及兩宋之際、北人為躲避金人攻擊而南遷有關。
至宋代,唐代原有的市坊界線已然瓦解,商業貿易突破原有限制,遍佈城市各處,甚至是超脫城市界線,發展到市郊地區,使城鄉之間的界線也開始模糊。同時,隋唐兩代的大運河溝通南北,成為交通貿易往來最方便的渠道。商業、交通貿易的發展,打破各地原來自給自足的情況,在宋代開始有專業生產區出現,大部分的城市、鄉鎮都被納入了此一市場機制,進行跨區域的買賣活動。
在此情況下,商人為了進行貿易,開始必須四處奔走。為了保護行商平安,他們在旅行中常會帶著家鄉所信奉的神像,祈求保守。這樣子的舉動無意間打破了傳統神祇領地的觀點。地方神祇開始隨著行商的腳步遍佈各地;而商人也在自己停留的地方為神祇修建祠廟,一方面方便自己的祭祀,另一方面也順便宣傳神蹟。若觀察宋代區域性神祇祠廟座落的據點,可發現它們有許多是作落在地方往來交通要道,這些地方常是商業貿易聚集的地方,是宋代商賈在四處經商、建立祠廟時,為現代的我們不經意留下的證據。
此外,北宋滅亡、金人大舉南親時,大量的北方居民為了逃難,紛紛南遷。他們在南方定居時,也不願放棄自己在原來家鄉所信奉的神祇,使這些外地來的神祇也開始在異鄉落地生根,發展在本地的祭祀。
如之前所提的,中國人選擇神祇的標準在於祂是否靈驗,如果一異地來的神祇仍可繼續顯靈,那祂便有可能贏得在地人民的祭祀,另外建立起一信仰據點。就依照這種過程,宋代區域性神祇陸續出現。
神祇領地的逐漸擴大,宋代神祇所具備的神力也開始有所不同。在農業地區,神祇所展現的神威多半是天旱降雨、暴雨天晴、蝗災驅蟲等和農業生活密切相關的神蹟。但隨著宋代商業的勃興,我們也發現在人民的禱詞中,出現向神祇祈求經商順利的語句;而在許多故事軼文中,也有許多神祇向其信徒透露哪些地方富有商機的消息。在在展現出隨著社會生活形態的變遷,神祇信仰體系也開始隨之轉換。莫怪乎也有人認為宗教只是人民心中想像的投射。
兩宋之際中國社會出現的巨大轉變,極大程度地改變了中國一般人民的生活樣貌;而宗教信仰作為人民心中欲求、想望最直接的投射,能反映出當世一般市井小民生活的需求、問題,也在許多部分受到當時社會環境變動的影響。雖然宗教作為一歷史研究的題材,在歷史學者追求客觀事實以及宗教本身就強烈地涉及個人主觀經驗的矛盾上,不免引起許多爭議,令人質疑,但它仍然為我們理解當時社會環境以及其支持者的生活情境,提供了一個極富創意的思考空間,就如同我們在討論宋代宗教以及中國在兩宋之際產生的巨大變動時所看到的一樣。
~ 參 考 書 目 ~
1. 韓森(Valerie Hansen),《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包偉民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生命的刀子刻下,不完美,卻也沒有敗筆 ,你我都是帶著殘缺的美麗靈魂。
誰在線上
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沒有註冊會員 和 79 位訪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