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帶一題,有空的話, 朱天心<古都> 可和日本川端康成<古都>搭配看,這便是文學上所謂的「互文」,大家可以去找找,書中出現的人名是什麼? 情節有何異同?以及台北與京都雙重或多重身世該如何解讀?
順帶一題,有空的話, 朱天心<古都> 可和日本川端康成<古都>搭配看,這便是文學上所謂的「互文」,大家可以去找找,書中出現的人名是什麼? 情節有何異同?以及台北與京都雙重或多重身世該如何解讀?
********************************
拋磚引玉,我先隨便談一下朱天心的<古都>好了.
構成「城市」(City)的歷史價值在於「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的特色,意即在於其歷史與文化的深度與複雜性,如同專業的地理資訊系統常用的「疊圖分析」(Overlay analysis) 一般,當一城市地圖中代表時間、文化、族群等面向的描圖紙「疊加」的愈多層,代表這城市是愈有生命力與文化。
朱天心〈古都〉如同可以不斷剝疊的羊皮般,見證著台北城市近代歷史,每一層都烙印著由底層社會所記憶的地景(landscape)。〈古都〉的重要性,早已在著名學者的繽紛論述中不斷被揭示和提醒,例如:楊如英談「互文」 、沈冬青論「故鄉╱他鄉」 、朱恩伶談「族群」 、張大春談「老靈魂」 、邱貴芬論「身分認同」 、梅家玲、駱以軍談「記憶」 、﹔王德威、唐小兵談「空間」 ,他們皆為〈古都〉一文開啟了多視角的討論。然而,這其中,令個人著迷的,以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或以脈絡閱讀(textual reading)的方式探究台北城及在地人的心靈,仍舊是一個空白與缺口,須待研究的填補。
敘事者如何從「明鄭時期﹕葡萄牙、荷蘭、西班牙」、「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四階段的歷史背景下,進行了一場台北歷史的調動,而這個歷史的調動對台北產生了一個「記憶再造」的動作。其次由村落的興起、以及日據時期建築、植物等多方向度,也可以抉出〈古都〉中「台北地景」展開的「現代/後現代」;「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個人/集體潛意識」;「主體/邊緣」等多重對話,因此,朱天心的創作與台灣經驗交集對話,一直保持高度的稠密度,也讓我們了解文學與心靈交織的複雜多向面貌。
********************************
ok~我一定要打住了,再寫下去就不可收拾 其實我好想看看大家的心得唷, 呵呵呵呵~大家趕快加油讀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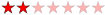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