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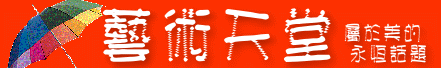 |
|
|
|
|
|||||||||||||||||||||||||||||||||||||||||||||||||||||||||||||||||||||||||||||||||||||||||||||||||
|
作者:林怡君 |
|||||||||||||||||||||||||||||||||||||||||||||||||||||||||||||||||||||||||||||||||||||||||||||||||
前言: 早在文字未發明之前,有關於死亡的形象於祭祀儀式、或是墓地壁畫等都廣泛的存在。儘管是書寫的紀錄方式出現之後,人類對於生與死的探討更是不曾間斷。藉由圖像所表達的死亡,仍舊是最豐富,也是人類在面對這個終極關懷之時最直接反映出自我的呈現[1]。每一個人都將有面對死亡的一刻,卻沒有機會再回頭描述這個經歷、紀錄所謂死亡的過程,只能用已知世界來想像這未知的將來,以熟悉的形式使無形的死亡具體化,同時賦予其意義,進一步更能夠理解、包容,甚至是正面迎擊、戰勝死亡[2]。 雖然死亡之不可避免的本質不會因著時空而改變,但是由想像力來呈現這「無法想像之事」的結果當然會在不同的時代、文化環境、民族人種之間產生不同面向的表現。神話、宗教、民間傳說、藝術、文學等等,都留下許多關於死亡的描述。本篇報告以繪畫藝術作品之中的死神形象(images ofDeath)為主軸,探討此形象在十九世紀末期,以女性作為死神之呈現方式的特殊變化。文章的第一部分將簡單整理從中古世紀以來死神形象的典型,以及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前半期此典範的改變。第二部分細看十九世紀後半時期,象徵主義藝術之中的死神形象如何被呈現。第三部分則試著探討造成世紀末死神形象轉變的原因。 第一部分:
在西方藝術與文學的領域中,古希臘羅馬神話以及聖經這兩大傳統一直是創作的源頭。羅馬神話裡死神的形象包括Thanatos,與睡神同為夜神的雙胞胎,常以優雅俊美的男性形象出現,倒拿著火炬(圖一);或是希臘神話中的冥王與引渡死者的死神(Pluto與Charon),以怪物人身的形象出現(圖二);或是三位命運女神(Parcae)中的可羅索(Clotho),命運之線的紡織手,不斷轉動巨大的紡車輪,以及負責測量命運線之長短的拉姬西絲(Lachesis),還有在生命將盡時,剪斷生命之線的艾托普絲(Atropos)。聖經之中的死神則包括了啟示錄[3]之中,拿著鐮刀的收割者(Grim
Reaper,圖三),或是四騎士當中的死神(圖四);以及作為上帝信使,拿著沙漏、頭戴皇冠、持有長劍的死神(King
Death,圖五)。除了古典神話與聖經,當然還有其他獨立於傳統圖像、自成一系的象徵,像是以骷髏骨架為代表的死神(bone
man,skeleton)等等。同樣的母題卻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形象在藝術作品之中一再出現,各個時代也有其關注的焦點。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初期人們的死亡觀與聖經的教導緊密結合,當時的核心觀念是:上帝創造人之後,亞當與夏娃的墮落、被逐出伊甸園,因為罪與墮落的代價是死,導致人類必須面臨死亡[4]。人類的原罪來自於亞當與夏娃背叛上帝,沒有遵照神的旨意,反而受到誘惑吃了生命樹上的蘋果,從此離開伊甸園直到生命終結之時才能再次回到神的國度。於是「罪」與「死亡」成為相對等的名詞,亞當與後人就必須為此原罪付出死亡的代價[5]。版畫作品中像是Hans Holbein的死亡之舞系列(Dances ofDeath,1538),一開始就以聖經創世紀裡創造、誘惑、墮落與被驅逐離開伊甸園為前四幅作品的主題,提醒人們不要忘了死亡的本質與源頭(圖六、七、八、九)。
時間書(The
book of hours)是中古歐洲使用的祈禱書,其中的插畫常見到典型骷髏出現,鐮刀與劍是伴隨死神的象徵(圖十、十一)。死亡除了與原罪、敗壞、威脅連結在一起,這個時期聖經啟示錄當中所提到的四個騎士,以及象徵王權的死神也出現常在文學與藝術之中,杜勒(Dürer,圖四,圖五)的版畫作品,展現了頭戴著皇冠的死神,騎馬揮舞著長劍,或是拿著沙漏數算人們將盡的年歲;在Jean
Colombe為時間書所做的插畫中(圖十二),死神甚至是以騎士裝扮出現,英勇的騎著白馬帶領裹著屍布的死屍大軍前進,讓俗世的軍隊潰敗且顯得驚恐不已。被無數戰爭、疾病、飢荒佔據了數個世紀的歐洲,死神形象如此權威性的存在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情形,由於死亡與亞當的原罪相聯繫,此時死神的擬人化(personification)也多半是以男性的形象呈現[6]。
文藝復興時期還出現另一種具有情色象徵意義的形象,以Hans Baldung(圖十三、十四、十五)與Niklaus Manuel(圖十六)的作品為例:在死神與處女(Death and the Maiden)一圖之中,年輕貌美的少女若無其事的拿著鏡子梳妝自己,與拿著沙漏的死神相呼應,身上的薄紗將被死神揭開,鏡子雖反映了死神的容貌,少女仍然無視旁人的驚恐,似乎正等待著死神來臨;死神與少女(Death and Girl)則描述已經被死神掌握的少女,無助的祈禱以及驚嚇不知所措的表情,順從的讓死神拉著她的頭髮引領;第三幅死神與女人(Death and Woman)情色意味就更加濃厚了,背景是刻著十字架的墓園,死神已經將女人完全擁抱在懷中,女人的動作則是將要解開身上的薄紗,恐懼的等待死之吻。Niklaus Manuel的死與處女(Death and the Maiden)之中,少女似乎不再懼怕,反而柔順的迎向死之吻,衣衫襤褸枯骨駭人的死神環抱著豐美青春的身軀,猥褻的手勢掀開少女的衣裙,探向曖昧的深處。死亡的親吻象徵了撒旦誘惑亞當夏娃咬下蘋果,死亡與性別羞恥的意識在背叛上帝的同時出現在這墮落的世界,在這個層面上,死亡除去威權、原罪之代價的內涵,反而成了撒旦與邪惡的化身[7]。 死亡之舞(Dance ofDeath, Dans Macabre)是另一個不斷被重複的母題。中世紀的手抄本曾記載,當歐洲大陸尚未完全轉化皈依天主教之前,在墓園中舞蹈是很常見的事。1493年Wohlgemuth的木刻版畫(圖十七)就紀錄了這樣的傳說:聖誕節前夕,當Megdeburg的St. Magnus教堂彌撒還在進行之時,有十八位男士與十位女士不理會教會的教導,在一旁的墓園唱歌跳舞。他們因此受到傳教士的詛咒,不能停止的一直舞蹈作為逞罰[8]。另一個傳說是描述三位貴族巧遇三死者的故事(圖十八),死者對這三人說:「我們曾是諸位現在的狀況,你們亦將變成我們這般光景」[9]。在這個故事中強調的是道德上教誨與訓誡,也開啟死神與生者之間鏡像(Double)的表達方式:帶領著人走向死亡的死神與生者其實是同一個化身,兩者之間的對比顯示出不論任何權貴都會面臨死亡,死者的舞蹈更是嘲諷人們為了世間利祿的奮鬥,再多的戰利品都終將消失幻滅。類似這樣的傳說不論是否真的是死亡之舞的來源,藝術家與文學家們確實從中獲得源源不絕的靈感而創作。目前存留下來最早石刻,1424年巴黎純真教堂(church of the Innocents,圖十九)
的死亡之舞,十六世紀Hans Holbein與Niklaus Manuel 的作品(圖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十七世紀Rodulf and Conrad Meyer兄弟的作品Todten-Dantz (圖二十四),十八世紀的J.R. Schellenberg的作品(圖二十五),十九世紀Thomas Rowlandson的The English Dance ofDeath (圖二十六),都沿用傳統的母題與表現方式,以骷髏形象代表死神,介入不同的群眾階級,不同的情境,在不同的時空文化環境也傳遞不同的意義。 到了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上半,死神的形象在萊辛(Lessing)等學者的論戰中又有新的呈現,萊辛的文章「古人如何再現死亡」(How the Ancients RepresentedDeath, 1769)指出,希臘羅馬時期的古典藝術當中,死神是愉悅、愛情、年輕俊美的少年Thanatos形象,一般人們認為是愛神(Eros/Amor)的雕塑,應該是代表死神,直到天主教的勢力介入,死神才轉變為令人懼怕的骷髏[10]。他在文章之中提到:「死亡的狀態沒有什麼好懼怕的,面臨死亡只是一個過渡,死亡本身並不恐怖」;又說「古代藝術家並不是用骷髏形象來呈現死神,他們是以睡神的雙胞胎兄弟同時描繪死神與睡神,兩者的相似性也讓我們很自然有相同的聯想」[11]。萊辛運用了古代石棺或紀念碑上的大理石雕刻,其中描繪的是倒拿著火炬的少年,神情姿態與睡神相似(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由此論證出現在藝術品之中的俊美少年應是死神(Thanatos),而不是其他學者所宣稱的愛神(Amor)。當時對於死神或是愛神的再現方式,Adolf Klotz則抱持相反的意見,認為愛神與死神完全不同,以不一樣的面貌呈現;與萊辛的論點較接近的像Herder,雖然兩者不能完全畫上等號,但是某些時候死神可以與愛神同一個身分出現[12]。這些爭論雖然沒有一致的結論,仔細觀察萊辛的論述也確實有疏漏之處,但不論如何都透露了這個時期的死亡觀,已經蘊藏了一種平靜、祥和、友善、甚至於是甜美的內涵。像是十九世紀音樂的作品當中如舒伯特的藝術歌曲「死與少女」(Death and the Maiden),也將死神描述為帶來寧靜和平的朋友: The Maiden: Pass me by!O Pass me by! Go away, wild boneman! I am still young, do go, dear man! And do not touch me. Death: Give me your hands, you beautiful and gentle form! I am your friend, and did not come to punish you, Be of good cheer! I am not fierce, You will sleep peacefully in my arms! 死亡本身不再令人畏懼,死神化身為美少男、愛人、或是朋友的同時,還與基督耶穌的就贖融合在一起。死神讓人遠離疾病、憂傷、痛苦等現世中的災難,帶來永恆的福音,以Novalis(1772-1801)的詩為例: Thou art the Youth who in our world of Tombs Hast stood so long, in solemn thought for aye; A Star of Hope amid the Night’s thick glooms, Announcing nobler Manhood’s dawning day: What darkened us with sorrow, now illumes And draws our longing eyes for earth away: InDeath the Life eternal is revealed; Thou art theDeath by which we first are healed[13].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死神形象不但與永恆接軌,也存在於每天生活瑣事之中。日常生活處處是危險的死亡陷阱,只不過人們依然是渾渾噩噩的度日,其實死亡就在最不經意之處。同時,死神與中世紀死亡之舞(Dance
ofDeath)所呈現的一樣,不論性別或社會階級都必須面對。但是不同於中世紀宗教與贖罪的意識,十九世紀國家政治環境的動盪,經濟社會的快速變化等等,反映在藝術作品之中的死神除去了中世紀那種令人懼怕的形象,添加了許多融入現實實際狀況,有時候甚至是幾近於可愛的特質。像是Thomas
Rowlandson的死亡之舞(The
Dance ofDeath),精準的諷刺了各行各業與社會各階層人士(圖二十九);Grandville的永恆之旅(
Journey to Eternity)這系列的版畫(圖三十)作於1830年革命的前夕,則呈現出當時布爾喬亞階級的生活,如同四處駛出的死亡列車,死神在當中喬裝成愛國者、社會主義、或是情色慾望等角色,無論是誰都不可避免的終究會搭上這特快車,人們生命之渺小短暫就像是在一觸即發的火山上狂歡舞蹈一般。
第二部分: 十九世紀上半時期著重於強調死亡的無所不在,與死亡的多重面貌,到了這世紀的後半,不論是文學或藝術,死神擬人化的的方式逐漸轉變。象徵主義、唯美主義、頹廢主義等世紀末的藝術中,死神在性別上的差異被突顯出來,呈現方式有兩種形象:死亡天使(angel ofDeath)及富有誘惑力的女人(seductress)。同時,母親的形象也或多或少的融入其中。之前並不是完全沒有以女性死神為圖像的慣例,如十四世紀Pisa濕壁畫上的死神就是披著長髮具有女性性徵的形象(圖三十一)。但是以女性的特質為主題,擺脫傳統宗教或是神話內容的表現方式,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才真的發揚光大。延襲十八世紀死神與愛神重疊的形象,死亡與愛情這兩個主題於十九世紀更加密切融合在一起,如同D.G. Rossetti 的詩[14],不需要古典藝術的神話寓意,直接將死與愛情認同: But a veiled woman followed, and she caught The banner round its staff, to furl and cling,-- Then plucked a feather from the bearer’s wing, And held it to his lips that stirred it not, And said to me, “Behold, there is no breath: I and this Love are one, and I amDeath.” 不同於過去以男性表現為主的死亡形象,Rossetti的詩明白的顯示出這個時期結合了女性與死神形象、愛與死。死亡天使(angel ofDeath)及富有誘惑力的女人(seductress),或是致命的女性(femme fatale),似乎承載了雙重涵義,包括代表死亡本身或是死神(Death),以及死亡訊息的傳遞者(messenger ofDeath)。Carlos Schwabe 1895-1990年的作品The Death of the Gravedigger(圖三十二)將死神描繪成美麗的少女, 從他早期版畫同一形象The Angel ofDeath(圖三十三),
可以確定這個少女就是與過去傳統形象完全不同的死神。圖中年紀老邁的掘墓者,正工作到一半時驚見死亡天使降臨,他似乎是訝異的看著蹲坐在墓旁的天使,任由纖細的樹柳與天使的翅膀輕輕環繞住。天使安祥的面容、輕閉的雙眼像是聖母一般,一手捧著冥世間的青綠色微光,一手指向天堂,似乎承諾著另一個極樂世界。掘墓人仰望的姿勢也像是期盼救贖到來,死亡成了一種美麗的拯救。背景是白雪覆蓋的典型墓園,塵世間死寂的白反而與死神的綠色調形成弔詭的對比,應該代表著新生的綠更讓死亡昇華為永恆的祝福。Carlos
Schwabe在這幅畫中曖昧的並置了少女與老者、死與生、永恆與時間流逝的對比、純潔神聖的聖母與敗壞枯朽的必死之軀等等,都顛覆過去固有的死神形象。
一樣是以女性為死神的擬人化,Jack Malczewski兩幅名為Thanatos (1989)畫作,蘊含更多的情色意味在其中(圖三十四,圖三十五)。Malczewski將原本是年輕男性形象的Thanatos變換為身材姣好的女性,優雅的姿態像是雕塑品一般的完美,但是她的翅膀、手上拿的鐮刀與磨刀石,都說明了死神的身分,放置磨刀石的小袋子懸掛在下腹部,暗示生殖的能力,更將死亡與性連結起來。這幅畫的背景季節與Schwabe的畫正好相反,草地與茂盛的樹林標示出春天或是初夏,正是萬物繁殖的季節。遠處的動物朝著古典廊柱建築靜靜的坐著,還有一位不知名的老者狀似寬衣,好像走向正等待著他的死神。另一幅同樣命名為Thanatos的作品,春天的氣息更加濃厚。身穿著火紅布袍的死神出現在陰森森的月夜中,一樣是拿著鐮刀的美女,背景突兀的開滿了百合花、紫丁香、鬱金香等象徵著愛情的花朵。死神回頭望著窗戶邊的老人,我們也不知道他是睡著還是死去的狀態,不論如何,對於死亡的恐懼在這兩幅畫之中完全不存在,Schwabe圖中仍存留的宗教救贖意涵,在此全都轉變為性與愛的暗示。 George Frederick Watts的畫作則是將母愛注入死神的形象之中。Death Crowning Innocence (1886—1887)這幅畫(圖三十六),死神除去所有威脅的象徵,只剩下翅膀溫柔的環繞著一個嬰兒。柔和的光線照在母親一般的死神,與安靜沉睡的嬰兒身上,整個色調是神聖的藍光,死神與死亡轉變成慈母呵護小孩入睡的溫馨場景。Time, Death, and Judgement (1884)一圖當中(圖三十七),
時間是健壯的青年,主持正義的女神飛翔在上方,死神則是白皙美麗的少女,戴著頭巾柔弱的垂頭閉著眼睛沉思,細膩的衣折表現出女性的順從與柔美,像是神話中的謬斯而沒有一絲令人害怕的威脅感。1870年的Angel ofDeath (圖三十八)之中的死神不但是女性,更是眾人引領盼望的拯救者姿態,Watts自己1893年對這幅畫的說明:「我賦予她一對翅膀,讓她看起來不至於像是聖母像。她懷抱著一個也許是無法來到人世的小孩,提供一避難之處。在她身旁有凡人看不到的沉默天使們護衛著,在死亡聖壇之下,眾多崇拜者加快腳步催促著:年邁的乞討者前來等待;貴族們獻出他們的皇冠;戰士們將刀劍卸下投降;貧病的小女孩更是緊緊抱住死亡天使的雙足。我希望我所畫出的死神是絲毫沒有恐懼在其中的[15]」。
Gustave Moreau的The Young Man andDeath (1865, 圖三十九),死神亦是以年輕少女的形象出現。前景的少男正走下大理石階梯,手拿鮮花與桂冠,顯露出健壯結實的體魄。後方是輕巧的漂浮半空中的女性形象,雙手持著寶劍與沙漏,讓觀者毫無疑問的指認出死神身分。男子手上的鮮花與前方散落地板的花朵形成對比,就如代表了成就的桂冠與後方的死亡象徵--這些象徵到底是指出短暫功名仍能凌駕死亡,還是指一切成就都逃不過死之幻滅?左下方的小天使拿著火炬亦是隱喻死神,右方飛離畫面的藍鳥,則象徵著離開身體的靈魂,都暗示了終極的死亡。整幅畫面華麗的色彩與夢境一般的氣氛襯托出古典象徵與聖經寓意複雜的融合,這裡所呈現的死神不但是柔美的少女,她沉思而憂鬱的面容讓畫面更多了些如詩的哀傷。 Alfred Kubin在1902年的作品The Best Physician將醫師的形象與具有致命女性形象的死神連結在一起(圖四十)。
一個將死的身軀平躺在床上,全身被裹屍布一般的白衣包住,雙手合十作祈禱狀與過度僵直延伸的雙腿顯得非常詭異;站立在旁穿著剪裁合身之晚禮服的女士,由骷髏頭顱就能指認出死神的身分,優雅且驕傲的伸出手蓋住床上那人的臉。這幽靈似的女性形象,也同時指涉了當時的醫療行為,是幫助人們更迅速的進入死亡的國度嗎?所謂最佳的醫師、最好的醫療、脫離疾病苦痛的唯一方法,在此與死亡、宗教靈性上的安慰、以及女性誘人但又致命的魅力全都結合在此畫中。Thomas
Cooper Gotch的Death
the Bride (1895)亦是曖昧的串連起純潔天使與致命誘惑兩個面向(圖四十一)。穿著黑衣戴著黑色頭紗的新娘,身旁滿是嬌豔燦爛,卻象徵著死亡與瞬息即逝的罌粟花;她微微地掀開面紗,慵懶的眼神與淡淡的笑容使觀者情不自禁的掉入她像是邀請、又像是拒絕的一團迷霧之中,同時,也陷進極樂、致命的泥沼裡。
以上的死神形象或多或少都有情色的意味,但是女性、死神、死亡與妓女的連結到了Félicien Rops (1833-1898)才可說是發揮到極致。關於充滿誘惑力的女子,或是街角邊接客的妓女,Rops精采的描寫了她們令人無法抗拒的吸引力。Death at the Ball (1865-1875,圖四十二)的主角是穿著日式外衣的骷髏,賣力的在舞會中舞蹈,身後若隱若現的一位男士,觀看、估算著商品一般的華麗展示,男性掌握了性別優勢與權力的同時也無法避免死亡的威脅。Dancing Death (1865,圖四十三)同樣是觀看與被看的結構,但是幾乎全裸女子的姿態與裝飾則更加粗俗,這個場景不是在舞會,卻很有可能是脫衣舞孃酒吧。頭頂帽子上俗艷的花朵掩飾了帽沿下的骷髏頭顱,掀開的短裙之下毫無隱避的買賣著性慾,一如波德萊爾的詩作--死亡之舞--所描寫的情景: Her eyes, made of void, are deep and black; Her skull, coiffured in flowers down her neck, Sways slackly on the column of her back, O charm of nothingness so madly decked![16] 第三部分: 中世紀的死亡觀聚焦於罪與墮落,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期強調撒旦與邪惡愛慾的角色,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前半的死神轉變成為與俊美的愛神雷同、或是像朋友一般,重視的焦點是追尋永恆與不朽。到了十九世紀末,什麼原因使得這時期的藝術家與文學家大量使用女性形象來呈現死亡?是如同心理學家與精神分析學家所說的「男人面對女性時的精神官能症」(”The neurosis of men vis-â-vis women”)?還是社會學家所說的,是男性對於當時女性主義勢力逐漸抬頭的一種反抗?或者是如同女性主義所提出的反駁,這種現象不過是表現了潛伏在男性心靈深處對於女人的恐懼,以及厭惡女人(misogyny)的情結,就如同中世紀將夏娃描繪成魔鬼的化身一般。這些理論都能解釋某些不同的現象,但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在此時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活躍於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佛洛伊德,在他筆下將死亡與母親形象直接連結起來。他認為依照男性與女性的關係可將女性分為三類:生殖者、陪伴者、毀滅者。這三種形象又必須以母性的元素呈現,於是就轉變成母親本身(生殖)、按照母親形象所選擇的愛人(陪伴)、然後是在人生終結時接受他的大地母親(毀滅)。希臘神話中的命運三女神與這三類形象也結合,在夢的解析一書當中,第一位可羅索(Clotho),命運之線的紡織手,她牽著線使男性得以存在,第二位負責測量命運線的拉姬西絲(Lachesis)則是賦予他能力,第三位艾托普絲(Atropos)是死神的化身,將生命線剪斷。佛洛伊德將誕生、命運、死亡人生的三階段與母親形象,連結死亡的焦慮,可以從全集中的一段話說明的最清楚:「如同最初從母親處接受的,年老的男人徒然地尋找女性的愛情,只有命運的第三位女神,沉默的死亡女神會將他抱在臂彎中」[17]。精神分析與心理學的發展使女性、母親和死亡之間的關係,從人的潛意識當中被挖掘出來,與藝術文學的再現也有了相當緊密的聯繫。 在社會學方面,Adorno與Horkheimer於1947年的”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提出,啟蒙時期科學進展使女性的本質與「自然」、「生物的循環」等概念密切連接起來,他們認為十九世紀末期的藝術家,Moreau、Wilde、Huysmann等,經驗到自然的威脅,並將其轉化、逃離到一種表面化的面具形式、以及過度人工化的形象之中:在作品中的女人被珠寶鑲滿全身,艷麗的彩妝掩蓋住原有「自然」的本質,過度的衣著則用來美化其下逐漸敗壞的身軀。同時,啟蒙時代對於女性性別的恐懼與壓抑還有另一原因:啟蒙時期將動物生物本能對立於人類的理性,女性若是接近於生物及動物的本能,就必然是不理性的,對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也同時是具有敵意的了。這樣的說法還可以進一步用西蒙波娃的論點來看,她將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投射追溯回男性更原始更根本的焦慮,也就是對於女性與生物自然之連結的不安。女性所展現的生物機能提醒了男性自身的生物來源、他被創造的源頭,因此當然也包括將來必臨到的死亡。女性所展現的生物機能--生育、月經、扶養幼兒、停經等變化,都顯示生物的一連串循環,也強調出生命誕生之後,不可避免的走向衰敗、毀壞等最終的盡頭。因此,代表了生命與愛情的女性與母親的圖像,同時也象徵了死亡的力量。她能給予生命,也能帶來死亡。在她的文章之中提到: 母親在給予兒子生命的同時,就預示了他的死亡;愛情誘惑愛人放棄生命,進入生命末期沉睡的狀態。愛與死之間的聯繫在崔斯坦傳奇之中深刻的被表現出來,其蘊含相當深厚的真理。男人以肉身降臨於世間,在愛情之中成就自身,這肉身也注定將走向最後的死亡墳墓。在此女性與死亡的結盟是確立的;孕育穀物繁茂成長的沃土與之後偉大的豐收就像是一體兩面缺一不可。收成者甜美但虛假的誘人外貌之下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神枯骨。[18]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醫學上關於身體與性別論述的改變,也影響了文學及藝術創作。十八世紀以愉悅和痛苦交織的性幻想,到了十九世紀轉變成以病理為論述焦點,與性別有關的疾病成為十九世紀人們了解身體的來源。持續著啟蒙時期對人體的了解,這個時期的身體觀將十八世紀神學中的敗壞與原罪轉譯為醫學上所了解的身體。1827年Karl Ernst von Baer於顯微鏡中看到哺乳類的卵子,此後對於性別差異的醫學觀點就專注在顯微鏡下的表現,所有原先肉眼「可見」的事物(seen)僅代表「外在」(surface),而原來無法看見,必須用科學儀器來顯現的「不可見之物」(unseen),才可以被稱為「真實」(real)。1858年Rudolf Virchow出版的Cellular Pathology就完全將疾病的根源從生理學上的解釋轉移到細胞層次,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必須從細胞的變化來了解。在這個架構中,病人,或是整個人體在醫學的研究之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顯微鏡底下的細胞,以及被肢解的身體。性別的差異也藏在細胞之中,就像疾病一樣根植於細
胞,如同定時炸彈一般等待引爆,成為所有病痛與敗壞的來源[19]。經由這樣的生理病理學知識基礎,十九世紀對於性傳染病的看法與解釋和過去大不相同:從顯而易見的外在疾病徵兆轉變成關注隱藏在細胞中的病源,從重視疾病本身所帶來的病痛轉移到注意導致疾病的「真實病源」,也就是與病人內在與生俱來的背景有關,更因之可使疾病的污名化變得理所當然、更易於接受。Virchow的Cellular Pathology將身體的隱喻擴張為精細組織的國家機器一般,不同階層的權力運作就像不同層次的身體組織,從細胞層次、各個器官、身體各部分、乃至整個個人。而一個敗壞的細胞,導致了敗壞的器官,整個個體也終將毀滅[20]。繪畫上的呈現明顯的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圖四十四),帶有梅毒疾病的女性成為死神與道德敗壞的象徵:骷髏頭顱隱藏在華麗服飾與美好的面具之下,小天使們飛翔在雲霧上方象徵著愛情,但是埋藏在布幕下的鐮刀,表明無法逃避的死亡威脅。 十九世紀末期生理病理學家、同時亦是醫師的Pauline Tarnowsky出版一本關於有關當時妓女之面像學(physiognomy)的著作。其中大量的描寫她們的頭顱形狀大小、頭髮與眼睛的顏色、身家背景、討論她們的智識程度、以及生活敗壞的狀況。關於妓女們臉孔特殊的異常表現也有詳盡的紀錄,包括:不對稱的臉形、塌陷或形狀不佳的鼻子、過度發達的側壁頭顱、簡化的耳形等等(圖四十五)。
這些特徵都說明最低等最醜陋的女性形象,也意指其接近人類最原始的本質,簡化的耳形則是挪用了達爾文的遺傳觀念,進而將這些特質合理化成為遺傳而來、也將必定傳遞下去的命運[21]。如此一來,就將從事特殊行業的女性與一般婦女區隔開來,所謂「正常」與「不正常」的階級劃分,讓男性對於原來不能掌控的疾病或死亡變成可以控制,或應該說是讓他們合理的認為主控了這些不可知的現象。Gilman更提出,這些關於性別、特殊行業、種族等等理論不只是控制女性的身體,還包括男性自我身體控制的投射;對於性別的控制,其實是反應了男性對於自身原始本質之控制的焦慮[22]。 在世紀交接前後,甚至是二十世紀都不斷出現有關女性的死亡圖像,或許是因為社會、生物學、心理學、哲學、文化上關於性別仍存在的雙重標準,再加上新興的女性解放運動上不能被接受,都使得女性成為當時社會主流文化之中,人類生命與社會一切罪惡淵藪的代罪羔羊。在這個世紀末以男性為主導的審判之下,她變成破壞力的化身,擁有著與身俱來的神秘力量,從事毀滅個人生命的工作,是宇宙中事物穩定結構的浩劫。本篇報告的最後引用同時是詩人也是醫生Gottfried Benn的詩,舉例說明當時高階知識份子所認知的死亡。這是Benn醫師於1912年描述一位溺死少女被解剖的場景,除了盡責做到解剖屍體發現並病因的工作,他將病理的描述紀錄成非常優美的詩句,將溺死的雛妓譬喻成死去的老鼠,而女人身體內的秘密表露了她自身的寫照--疾病的來源、罪惡的淵藪、死神的化身: The mouth of a girl, who had long lain in the reeds looked so gnawed upon. When they finally broke open her chest, the esophagus was so full of holes. Finally in a bower below the diaphragm they found a nest of young rats. One of the little sisters was dead. The others were living off liver and kidney, drinking the cold blood, and had here spent a beautiful youth. AndDeath came to them too beautiful and quick We threw them all into the water. Oh, how their little snouts squeak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