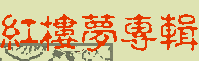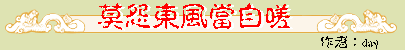|
 |
|
|
|
|
|
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前世身分,是一株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絳珠仙草,便暗示 了這個形象是由「血」「淚」凝鑄而成的。曹雪芹自述所作的紅樓夢說是「一把 辛酸淚」,「字字看來皆血」,而林黛玉正是這部血淚之作的精魂。百年來對紅 樓夢的讀者來說,林黛玉孱弱的病體承載了人間所有情愁的重量, 一己的悲劇成 為了人間永恆的憾恨,她究竟是如何牽動眾人心中深處的那根弦?
紅樓夢中每每將釵黛並舉,相對於寶釵從外在到自身都是當時社會價值的完 美賦予與形塑,黛玉很明顯是作為內在性靈本質一端的代表。而性靈的根柢是幻 情榜中的「情情」二字,從下世為人是為償灌溉之恩的情債始,到為情瘁盡心力 淚盡夭亡止, 黛玉為情而生為情而死,終一生都可說是為「情情」二字作註腳。 除此之外,可說別無所有。
在小說中,很明顯除這些本質性的價值賦予黛玉生命的定位外,作為一個寄居 親戚家中無家可歸的孤女,她是沒有任何外在社會價值的定位中所能給予的依恃 的。環境所與的條件如此,但黛玉卻不選擇去追求和攀附這樣的依恃。相反她更 堅持作一個自然人的本質的要求與完成,所以當寶釵謹遵德容工言的規範而行時 ,黛玉是在瀟湘館中讀書作詩,追求她的性靈生活。寶釵裝愚守拙安分隨時,她 卻安心展技,將眾人壓倒。雖然有禮教規範的重重壓制,她仍堅持獨佔寶玉的感 情,當著眾人直發她的妒意。當眾人有默契地對應所避諱之事緘默時,她直指底 蘊。自始至終都堅持「質本潔來還潔去」維護本質的要求。
這樣的堅持在人世所註定的結局是覆亡,不避諱地和寶玉爭吵是赤裸地顯示 對寶玉的在意;和寶玉特別親密的關係在小時上可藉著兩小無猜而遮掩,長大後 卻不能避免眾人的猜疑與側目。口齒尖利直陳事實換來的是「嘴裡又愛刻薄人」 的惡劣評語;不肯與人虛偽應酬,本性懶與人共便順性而為,卻給了人「孤高自 許,目無下塵」的孤僻形象」看她教香菱學詩一副熱腸,和紫鵑之間更是超越了 主僕的情份,說明了她的情情,只能情於情,不是出於真情的交接,她是不為的 。
林黛玉用著生命所呼喊堅持的「情情」,現實中是無法有立足之地的。在賈 府這個「詩禮簪纓」的大家族中,曹雪芹一面描寫這個家族是如何講究著具體的 繁複禮教規範,甚至成為滲入到人物在日常習而不察的氛圍和心理中﹔另一方面 ,他又赤裸裸地描寫家族中遮蓋在禮教背後的種種「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 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的骯髒污穢,兩相對比出禮教的虛飾性。但逸出禮 教規範的兒女真情,卻反被視為「不才之事」,而被嚴加禁防。當禮教成為維持 社會機制被假借的寄託時,個人便得被要求為禮教之名犧牲,以全大局。小我的 存在在大我的要求下,是必須消沒的。而黛玉的「情情」,是在呼喊著作為一個 人本質要求的成全,當黛玉說「我為的是我的心」時,這極端自我實踐的話語是 讓環境聽得不太順耳的。
從賈母的態度來看,她對兒孫們的疼愛並不是虛偽的,透過薛姨媽的口,可 以知道賈母疼黛玉是賈府所共知的事,寶黛嘔氣時,她「抱怨著也就哭了」﹔元 宵節放鞭炮黛玉不禁畢駁之聲,賈母便摟她在懷裡。對寶玉愛混在女兒堆理,雖 則仍不解是什麼樣的毛病,也能理解到不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比 較起賈政對寶玉以淫魔色鬼相視,顯然她對寶玉的性格並沒有基本的錯誤理解。 這樣一個慈愛的祖母,以著賈家的最高家長的身分迴護著寶玉和諸釵,但她同樣 也是賈家宗法的最高維持者,對於寶玉的婚事,不能想像不善與眾人周旋應酬, 工愁善病,口角鋒利的黛玉能得到她的首肯成為寶二奶奶,擔當作為賈家媳婦的 持家重責。畢竟婚姻決定的著重點在對整個家族秩序與利益的考量,個人的兒女 私情不能作為考慮的決定。賈母作為賈府的太上君為賈府整體考量而捨棄黛玉是 很自然的事,作為當時社會價值的實踐者,賈母並無可非議之處。因此黛玉的悲 劇便不得不然,縱然令人憾恨卻又無可奈何。
「莫怨東風當自嗟」,黛玉不能對環境辯駁,又不能遁逃天地之外,世外仙 姝為了作為一個自人對情的完成和堅持而下世,但人世卻竟無她的容身之所,「 情情」二字最終竟只能用自己的生命與血淚來完成與見證,作者用黛玉的死來扣 問,這只能是一個悲哀而無解的命題嗎?
歡迎和我們聯絡:gospel@life.fhl.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