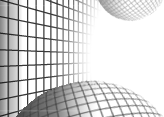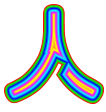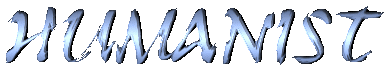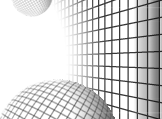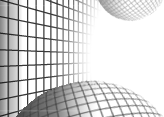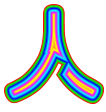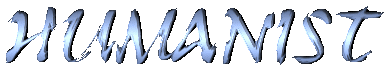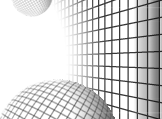|
羅素悖論的發現並不容易,但是這個悖論本身卻是極其簡單與明確,只涉及了集合論的基本知識。這使得大數學家希爾伯特十分震驚,說它會給數學帶來「
嚴重的災難性後果」,塔斯基也稱它為現代邏輯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集合論與演繹邏輯作為數學的最基礎(這兩者當然更是理性的基礎),接踵而至的集合論悖論於是引爆了數學的第三次危機,這個危機的本質在於,素有最嚴格科學之稱的數學,其整個大廈的基礎竟然是自相矛盾的。當時數學界對於悖論的根源與解決途徑,出現了眾說紛紜的混亂局面,剛好那時候也正是「古典物理學的危機」--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提出。羅素認為作為一個好的悖論解決方案,最好能夠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個是矛盾必須消失,第二個是數學體系盡量要原封不動,第三個是解決方案是「非特設性」或「非人為性」的。
研究數學家與哲學家們企圖解決悖論問題的過程是很重要的,因為解決方案意味著要對理性運作的基礎做出總體檢,同時他們要指出理性矛盾的根源。羅素最初的解決方案是類型論,其精神類似於他試圖解決說謊者悖論的方法:區分不同層次的集合,例如「集合的集合」(以集合為元素的集合)與「集合」是不同的層次,不能相互歸屬或代換。這個解決方案雖然排除了羅素悖論,可是有些結論卻與人們的直覺相違背,例如自然數中的0、有理數中的0與實數中的0居然是不同的類型,同時類型論也使得其他無害而重要的數學定理無法證明,違背了羅素自己提出的第二個條件:數學體系盡量要原封不動。羅素對於自己的解決方案感到失望,不過藉由羅素的嘗試,使得後來數學家的解決方向是趨向表述:要限定一個整體之中不能含有那種只能借助於這一整體才能定義的元素。最後的明確方案是根本性地斷言:「所有集合的集合」不存在,而不是羅素當初所採取的「所有集合的集合」與「集合」是不同的層次。換句話說是,在集合論中無條件地排除「所有集合的集合」,或者說是排除某種無限的概念,規定理性不(能)去處理這個概念,這就是後來的公理化集合論,公理化集合論還有好幾個不同版本,這是由於前幾個版本還無法完全杜絕已知的悖論,這段數學上極富爭議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雖然我們藉著重新「限定」集合的定義,以避免已知悖論的出現,但是問題是這種做法是不是「特設性」的?我們只是為了挽救數學(理性)基礎而限制某些概念,還是我們有其他更「合理」(哈!當寫出這一詞彙時,還真像是理性本身的自我指涉)的與更根本的理由去限制這些概念?可是不管有多少的爭論,我們還是必須在基礎上給予集合論或理性本身這樣的「侷限」。
所有不同類型的悖論都被適妥地解決了嗎?或者人們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悖論嗎?直至今日,不同類型的悖論問題本身仍然沒有公認的圓滿解答。值得注意的是,藉著研究說謊者悖論所帶來的靈感,哥德爾在一九三一年關於形式系統與算術系統的不完備定理,宣告了從形式技術上徹底解決悖論問題的不可能性,換言之,雖然數學界排除了已知的悖論,但是並不代表其他悖論不會在未來發生。這個結論是哥德爾當初簡直不敢置信的。哥德爾通過句法和語義的互相「層次糾纏」,證明了足夠複雜的形式系統存在著本質上的侷限性。他證明了:(a)一個形式系統S如果包含形式算術系統作為子系統,它就是不完備的,即存在著一個命題A,A與非A在S中都不可證,這被稱為第一不完備定理。(b)如果這樣一個系統是一致的,那麼其一致性在系統內是不可證,這被稱為第二不完備定理。又由於形式系統是演繹系統的最高形態,所以哥德爾也揭示了演繹科學理論與方法的侷限性,這消息就像是數學自身證明了自身的內在缺陷。
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在不同的領域引人注目,其地位就類似於物理學中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電腦程式語言的丘奇-圖林之不可判定定理,形式語言中塔斯基的真概念不可定義性原理,以及語言哲學中蒯因的翻譯不確定性論題,它們都在不同的方面界定了認知或理性能力的範圍。連同著幾個領域(語言哲學、語義學之真理理論與意義理論、複雜性科學、碎形理論、系統理論……)的整體論觀點,恰恰說明了不同系統的概念彼此依賴,而理性根本無法實質上窮盡這些系統的概念或者單一地把握個別系統的概念,任何系統的真理性或價值永遠都被鄰近的系統所聯繫或者被更大的系統所涵括。這些觀點都表示了人們在運用理性能力時的處境。寫了啦啦一長串,最後想要引述筆者在《上帝全能的論辯與理性認識的侷限》討論串的一段話:筆者所想要論述的是個很龐大的問題,寫個幾萬字都可能還有得討論與更深一層的研究。筆者只是把這樣的討論視為一個開端,而且是重要的開端。後面附上筆者在《上帝全能的論辯與理性認識的侷限》這個討論串的主要內容,以做前後呼應,只是筆者刪去了這中間一些細瑣的討論內容,所以有些段落的上下文顯得不是很有連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