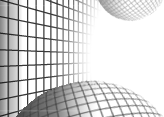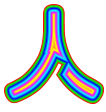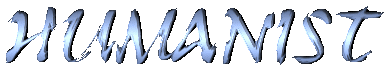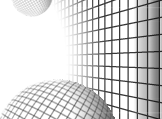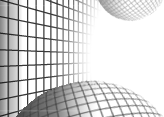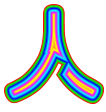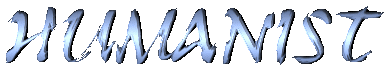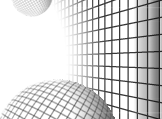|
前一陣子在哲學連線板,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有一天,撒旦跟神開了一個玩笑,撒旦跟神說:神啊,你是全能的吧,請容許我一個請求,請神變出一個你跳不上去的山!撒旦對神說:連我的請求都做不到,你真的是全能的嗎?這個討論串,後來在哲學連線板有了好幾篇的激烈討論,直到現在還有零星的後續火花(見「詭異的邏輯」之討論標題)。
這種上帝全能的論辯有著許多的形式,最有名的是:全能的上帝能否創造一顆自己搬不動的石頭嗎?上帝如果能創造一顆自己搬不動的石頭,那麼無法搬動這顆石頭就證明上帝不是全能的;如果上帝不能創造自己搬不動的石頭,那麼祂也不是全能的上帝。雖然這個論題無法推導出兩個相互矛盾的命題而形成嚴格的悖論形式,可是卻也意味全能的概念在邏輯上暗含著矛盾,或者說這一詞彙無法被人所把握。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問,來突顯這個問題的尖銳性:「全能可以使自身不全能嗎?」
這類問題不僅在神學界惹起一陣風波,也使得數學家們頭痛。這類問題如果在邏輯上使有神論威信大減,那麼它也搞得數學領域天翻地覆,因為類似形式的矛盾問題造成了二十世紀初的第三次數學危機,表現在數學上的例子是羅素悖論
(集合論悖論),它有一個大家比較知道的變形,即理髮師悖論:在薩維爾村有一個理髮師,他掛出了一塊招牌規定著:「我給而且只給村民中不給自己刮鬍子的人刮鬍子。」於是有人就問他:「你給不給自己刮鬍子呢?」無論這個理髮師怎麼回答都會產生矛盾,這是個嚴格的悖論形式。
這類矛盾的問題無論是神學家還是數學家都會感到困惑,到最後我們會發現
:像這種自身與自身矛盾的問題,人們的理性是很難處理的,就像是以電腦程式模擬說謊者悖論的時候,程式會陷入無窮的真假震盪之中,而永遠得不到最後的真或假的斷言。它們都牽涉到對於無限(全能也表現為一種無限)、無限循環與自我指涉的認識。
目前數學界對集合論悖論的根源的處理方式,只是把它給無條件地「排除」掉,而不是去「解決」它。有人問我「排除」與「解決」的差異何在?對於羅素悖論(集合論悖論)的處理方式是建立公理化集合論,例如所謂的ZF集合論公理系統,它處理悖論的方式就是特別規定形成集合的條件,例如不允許,也就是排除「所有集合的集合」這個概念的存在,而這個概念即是產生集合論悖論的根源。這種處理方式就像是,我們知道悖論的存在,無法解決它,只好規定大家不要去討論它而迴避它,這即是文中「排除」與「解決」的差異。用迴避法「全力封殺」悖論雖然有效,可是對數學家來說悖論的打擊仍是深刻的,因為他們知道悖論還是在巷子外,他們知道如果不作特別的規定,那麼悖論會隨時出沒--數學界選擇的做法就像是對它們視而不見。
而對神學界來說,他們解決的方法是提出一個不同於原本的邏輯定義的全能概念:全能在邏輯原本的定義是「無所不能,無論怎樣都能」,而神學界對全能的定義是「無所不能,但是不能背乎自己」。這跟數學界處理集合論悖論的做法很類似,都是先把產生悖論的那個根源給無條件排除掉,要大家不要去討論它。
如果硬要請神學家作邏輯上的解釋,對於神學家而言,可以這樣說:這個問題只能在邏輯上證明上帝不是全能的,或邏輯上全能的上帝並不存在,但是這並不證明「上帝不存在」!上帝是不能背乎自己地全能,而不是邏輯上的全能。或者神學家也可以提出所謂的全能或無限,原本就不是人們所能認識的,所以關於上帝性質的有關問題人們無法回答。
如果我們進一步地談,在這些問題底下,神學或數學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危機
,那麼這是揭示人們理性能力的侷限,在這裡這個侷限出現在對於上帝性質的認識與對於自我指涉的反覆矛盾的困境之中。在這些困境裡,我們會陷入無窮反覆的圈圈
, 就像是荷蘭版畫家 Escher 畫中的怪圈紙帶, 紙帶扭轉一百八十度而首尾相接的結果,我們會從紙帶的正面走到反面,再由反面走到正面,不管怎麼走
,怎麼努力,在不對某些概念設下限制的狀況下,人們對於上帝性質的論證與無限概念自我指涉的論證,還是會落入反覆的困境裡。
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宗教權威逐漸遭遇懷疑,到了當代,自然經驗科學也在歷史學派的反撲下,被突出了非理性與社會化的那一面,在這樣的混亂氣氛中
,當時的數學還是被公認為理性堡壘中最穩妥的立足點。可是數學家們後來發現
,不僅有悖論所帶來的問題,就連數學的真理性,它自己也無法自圓其說。
當代的形式邏輯學揭示了:如果我們要證明數學理論的相容性或完備性(這兩者被視為數學真理性的要求),必須要依靠該數學理論以外的論據,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大的系統來說明理論本身是真的,在此之前,我們還需要更更大的系統來說明那個被擴大的系統是真的……到了最後,無一處是獨立的真理,因為每一個系統的真理性都依賴於其它系統的真理性,這個特徵不僅表現在數學之中,也表現在人類的所有語言形式之中。
對於一個足夠複雜的數學理論,並非所有的真命題在系統內都是可證的,就連其一致性在系統內也是不可證。某個程度可以這樣說,當我們指出某個理論系統是真理性的,最低限度有其信念的成分,在那些不能完全證明的地方,我們仍然相信它,這不是僅有理性能夠作到。我並不抬高神學的地位,也不抬高數學的地位。真理雖不被全然認識,可是作為一個信念,我們相信它是可以被追求到的
;同樣的,我們應該也能理解神學家的信念,上帝雖不被全然認識,祂卻存在。
|